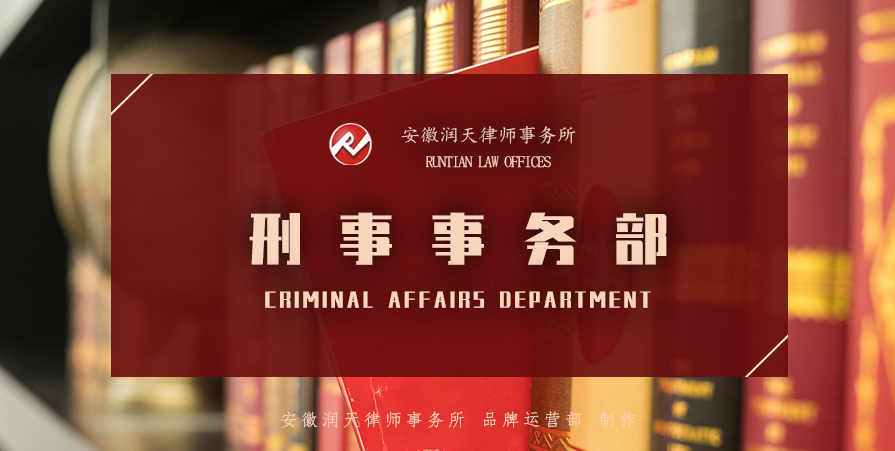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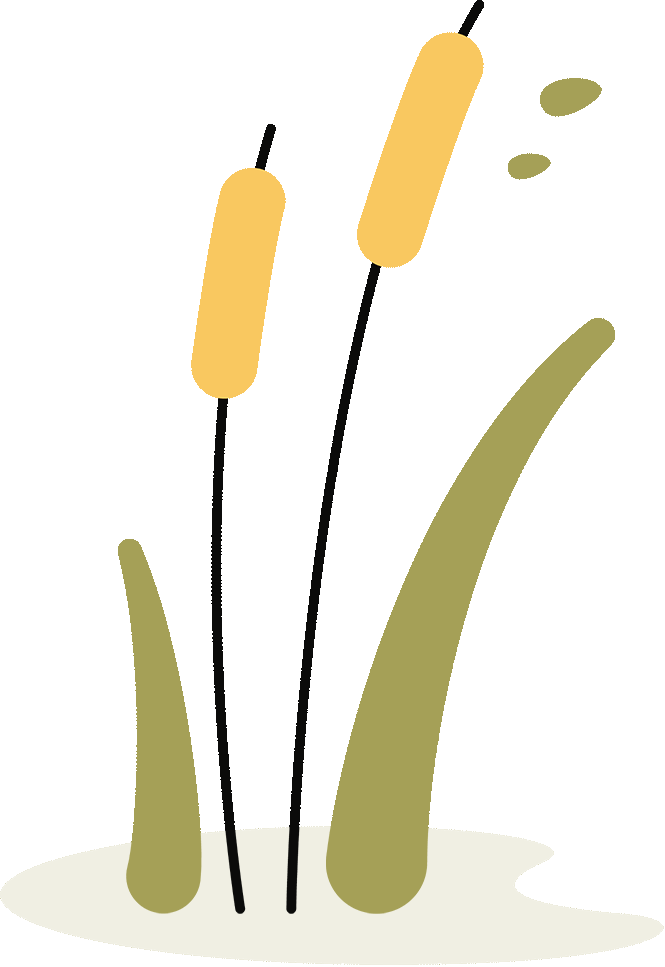
刑法对交通肇事罪规定了三个量刑档次,其中肇事后逃逸为第二层量刑档次,也即交通肇事罪的第一个加重情节,同时交通肇事后逃逸承担了连接基本情节和最后一层加重情节的重要使命,对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正确理解关系到交通肇事罪条文的整体适用,而对交通肇事后逃逸这一情节本身也需要限制性地理解,不可盲目扩大其适用范围。
一
前提限制
对于何谓交通肇事后逃逸,有专门的司法解释对其进行了大致的解释,司法解释的规定: “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 2 条第 1 款规定和第 2 款第(一) 至(五) 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本解释中的交通肇事和刑法交通肇事罪条文中的逃逸都是以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基本犯为前提,行为造成的后果需要符合交通肇事罪基础情节,也即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死亡三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或者交通肇事虽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但同时具备其他法定情节的,而在这些法定情节中,逃逸也在列,如果行为人造成一人重伤且逃逸的,只能认定为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而不能适用加重情节,否则既是对行为重复评价,也不符合罪责相适应的原则。
关于基本犯的限定并不能说是理论性的解释,而是从立法的逻辑与刑法条文的行文原则,本就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因此不应当存在争鸣。在行为人构成基本犯的前提下,如何认定逃逸,在加重情节的层面如何进行理解才是问题。如果说简单粗暴地理解为离开现场,那么便会产生许多现实适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对逃逸的解释为为逃避法律责任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也仅仅在简单的直接理解上添加了逃避法律责任这一限定条件,并没有为交通肇事后逃逸能够作为加重情节提供正当性依据,同时带来了犯罪后逃逸本身就是不能加以加重处罚的事由,为何交通肇事后不能逃逸、行为人未逃逸的又能否认定为自首等问题。对交通肇事逃逸加重处罚便需要一个特别且合理的理由,而未经这种解释就直接作为一个司法解释中的认罪依据,也是存在问题的,可以说,依据本身就有问题的解释去解释一个问题,所得出的结论也必然没有说服力。那么何为逃逸在司法解释不力的情况下,便需要通过理论解释对其内涵进行明确。而根据交通肇事罪条文的特点,目的解释和体系是一个相对可取的方法。
二
体系性解释
首先在条文体系上进行解释,关于交通肇事罪整个条文,理论界一直有一个集中讨论的问题,即交通肇事罪这一条到底规定了一个什么样的行为类型,三个量刑层次,涉及三个行为,交通肇事、逃逸、逃逸致人死亡,而后两个情节又不能被评价为交通肇事,更由于其分别是交通肇事行为已经终了之后的事后行为和事后行为所导致的加重结果,将其放置在交通肇事罪的罪名之下,又不能不将其解释为加重情节,于是就导致了不能自洽又不能忽视的矛盾。纵观整个条文,可以说其指向的其是两个独立的行为,即交通肇事行为和交通逃逸行为,交通逃逸行为并不是交通肇事行为不法性的加重,因为交通肇事行为的不法性在不法后果出现之时已告终结,逃逸所呈现的是另一种不法性,虽然在事实逻辑上有关联,但在不法性评价上应当割裂地予以看待。应当说交通肇事后逃逸需要刑法规制的的,本应按肇事逃逸罪进行规制,而不是直接安插到交通肇事罪中只作为一个情节。
但既然现行刑法已经作了如此的规定,那么对逃逸情节就需要在条文内部进行体系性的解释,即交通肇事罪所规制的并不是单纯的交通肇事行为,而是包括肇事后一系列能产生法益侵害的行为的类型总和,包括基本的违反交通规则导致的肇事后果以及导致更多关联后果出现的行为,主要也即是导致交通肇事后果进一步扩大的行为,而逃逸行为在其中所起到的就是导致肇事结果进一步扩大的作用,是连接肇事后果与扩大后果的桥梁行为。
那么在实质上,逃逸行为所具备的一点就是逃逸行为应当能使肇事结果进一步扩大的行为,而不能是单纯的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如果被害人已经全部死亡,行为人逃逸的,因为基本肇事的结果已经不能进一步扩大的,因此,这种逃逸行为不应当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行为。反之,几名被告人身受重伤的,行为人明知但为逃避追究而对伤者不闻不顾离开现场,在结果上,是放任重伤结果向死亡结果的发展,在主观上,由过失犯罪向故意犯罪转化,因此,对其加重处罚并无问题。同样的,如果行为人已经履行了必要且充分的救助义务后离开现场的,也不应作为加重情节予以处罚,如行为人发现肇事之后立刻报警,并躲在暗处暗中观察伤者情况,等救援人员到达后才悄悄离开的,也不能认定为交通肇事中的逃逸。因此,可以说,行为人只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的,不能构成逃逸加重处罚的依据,对于“逃避法律责任”中的法律责任,应当就解释为防止结果进一步直接扩大的责任,而不包括法律追究的责任。只能说,行为人不履行法定救助义务的内在动因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但这种事实归纳并不能成为不法性认定的根据。
三
目的性解释
在目的解释上,可以大胆猜测,之所以出现肇事与肇事逃逸的杂糅规定,主要目的也是因为逃逸行为的多发性和对结果扩大的直接关联性,立法目的也就是为了防止这种多发的扩大型后果的出现,而并不是为了倒逼行为人主动投案,接受调查,否则既不符合期待可能性的基本原理,也使本类案件中自首的认定出现困难,又或者说,将逃避法律责任中的责任理解为主动投案,无异于是在说行为不自首的,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使得自首的鼓励式设定成为了强制性的设定,这当然也是不合理的,尤其为某一个个罪进行这样的制度调整就更加不合理。顺着这种立法目的,行为人履行了救助义务但没有主动使自己被控制的,并没有违背立法初衷,只要行为人没有使结果进一步扩大,也没有导致其他后果出现的,无论行为人怎样逃逸,用什么方式逃逸,都不是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
四
法益侵害视角
最后从法益的角度来看交通肇事逃逸,一个不产生法益侵害、没有增加法益危险的行为,不足以由刑法来规制,在交通肇事后结果已经定型,不会在产生新的危害结果的情况下,交通肇事逃逸并不会产生新的法益侵害威胁,也就不能惩罚这种行为,更不能作为加重情节。至于肇事后能否给法律责任的追究带来阻碍,不应该作为交通肇事罪所保护的法益。放眼刑法分则,除非是替他人掩隐、包庇等阻碍法律事实查明的手段,替自己破坏、隐藏证据都不作为犯罪处理,更何况单纯地逃离现场,因此,将交通肇事逃逸的侵害法益片面地理解为法律责任的顺利追究,并无多少合理性。而将其保护法益理解为交通肇事受害者的生命法益,将逃逸理解为救助义务的违反,则对整个交通肇事罪的条文解释都能有一个能一以贯通的逻辑。

★
杨宜 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