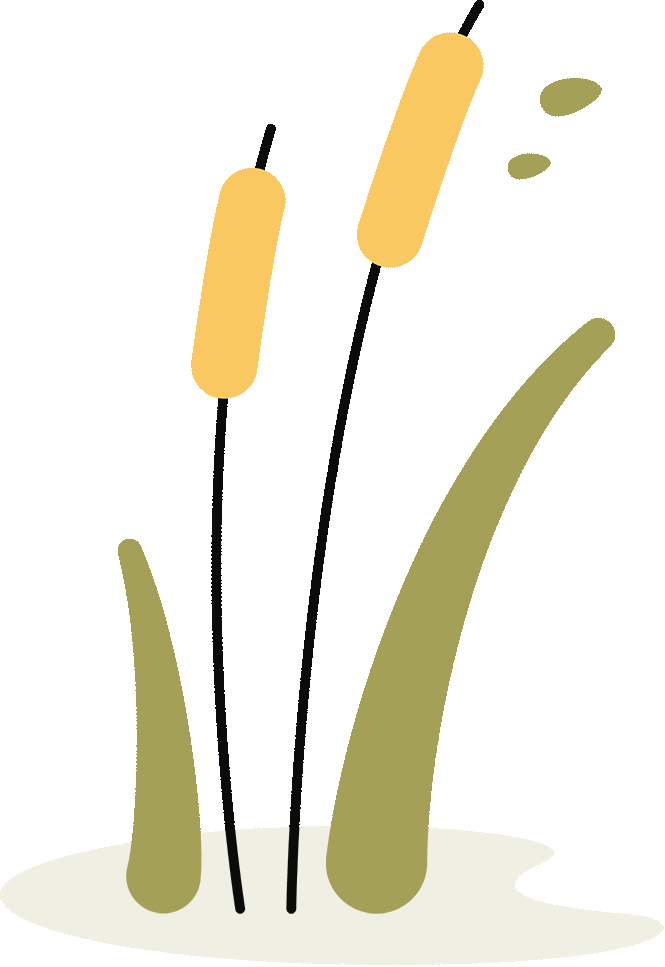
正确认识交通肇事罪中的因果关系是认定行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关键,作为常见类犯罪,交通肇事罪的形象并不模糊,但其因果关系却是一个容易被忽略或者被混淆的问题。关于交通肇事罪的因果关系,涉及到基本犯的因果关系、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因果关系以及逃逸致人死亡的因果关系。怎样认定交通肇事符合刑法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怎样正确区别刑法与交通法规认定的责任 ,逃逸致人死亡的因果关系判断中第三人介入和合义务的替代行为,是交通肇事罪中三个比较明显的问题。
一
违反交通管理法规与肇事的因果关系
关于交通肇事罪的罪状,其条文明确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立法明确了构成交通肇事罪的一个必要前提是违反交通管理法规,并且违反交通管理法规是导致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在按照交通规则行驶的情况下发生的意外事故不为交通肇事罪。虽然这样说看似无论是从常理还是出发都是很自然的结论,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对于违反交规而导致发生重大事故这一因果发展过程,其理解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就能达成一致。
首先是违反交规而导致发生重大事故这一前因后果的问题,常常容易在认识和论证的顺序上陷入混乱,出现以果定因或者循环论证的问题。比如说,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先认定结果符合交通肇事罪的结果标准,再根据结果倒推行为人一定违反了交通管理法规,又因为行为人违反了交通管理法规,从而导致了交通肇事罪,因而行为人构成交通肇事罪。这样认定的逻辑就是,只要在交通肇事中出现了相应的结果,就会被认定为交通肇事罪,即使行为人是在慌乱中错将油门当作刹车、撞到突然出现在路中央的行人,都会以违反一定的驾驶注意义务为理由认定为违反交通管理法规。但问题在于,如此就会导致驾驶人员承担过重且过宽泛的注意义务,有些行为也难以或不应该被归类到注意义务当中,如慌乱中将油门当刹车的问题,行为人在并非是出于不注意或者无所谓的态度而将油门与刹车混淆,而是慌乱中失去思考和判断能力,不能再去注意。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如此认定,等于将肇事行为与注意义务违反行为的认定混为一谈,导致肇事行为存在就是注意义务违反,如将油门当作刹车这一行为,就既是肇事行为,又是注意义务违反行为,如此,就不会再关注行为人是否真的违反了一定的注意义务,也不会关注行为人在当时的情境中是否有注意能力和结果回避能力。
另外对于基本情节中的因果关系,还有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就是违反交通管理法规与发生事故二者之间应具有刑法上直接的因果关系,也就是在事实的因果关系上还要进行规范的限缩和排除,反向的不构成的例子如某人在多个路口闯红灯,但在闯完最后一个红灯并行驶了一段距离之后与某人相撞,虽说此人如果之前不闯红灯就不会刚好出现这个地点发生事故,但不能认为事故与闯红灯与事故有刑法上的可归责的因果关系。
二
交通事故认定书与因果关系
《道路交通安全法》就有这样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交通事故认定书是认定事故成因和责任的重要依据,是认定交通肇事罪责任和因果关系的参考。虽然在实务中其是一个参考,但毕竟行政法上的认定能否作为刑法上犯罪成立与否的认定依据不能不说是一个问题。在法领域的跨越上、认定标准上和保护目的上,行政法与刑法都存在着鲜明差异,直接照搬行政领域的认定结论而不进行刑事方法上的二次审查,必然会导致不合理的结论。例如,在行政责任的认定上,二车相撞,都无过错的,承担同等责任,这里的同等责任结论当然就不能直接照搬到刑事责任的认定上,否则一个无过错的行为人就要承担交通肇事罪的责任,显然不能允许。
刑法上的责任需要过错的存在,而不仅是单纯的结果划分和事实因果力的推导,正如前述,有事实因果关系的,不等于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实体上差异如是,在程序上差异亦应如是,行政责任的认定标准与刑事事实的认定标准其原则性与严格性也不同,交通责任的认定基本上根据现场的情况就能作出,当事人不复议的,也就是最终结论。而刑法结论的确立则需要完整的证据链、排除合理怀疑,并且在证据的采取和收集上需要按照严格的程序和手续,相比之下,事故责任认定书就显得随便和松散了一点,不能作为刑事事实和责任认定的依据,只能和通过刑事手段采集的证据配合使用,作为辅助判断的参考材料,而不能作为主要判断。
三
逃逸致人死亡的因果关系
逃逸致人死亡中的因果归责问题涉及的最具争议的问题是第三人介入和合义务的替代问题,前者涉及的是逃逸之后伤者因得不到及时救助又被后来的肇事行为致死的,前行为的责任是否断裂,后者涉及的是,行为人虽然有肇事行为,但即使行为按照法律的期待实施了一定的行为,结果仍有可能发生的,行为人还是否依然由行为人负责。
对于第三人介入的,最终的死亡结果由第三人所导致,前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链条似被切断,但这样是在只观察行为与结果的情况下才得出的结论,完整地观察行为到结果之间全部的过程,行为人的逃逸行为与结果、第三人介入的行为与结果这两条因果主线并不是互相对立而是可以兼容并作为一体看待,也即第三人行为的介入不是由逃逸人引起和支配,但第三人肇事的影响力能够施加到被害人身上,与前行为人的逃逸行为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没有前行为人的逃逸行为,第三人的肇事行为也就不会导致被害人被害。可以说前行为人与肇事人并不是独立的因果关系,而是叠加的因果关系。但如果后行为是故意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则第三人全力支配了因果关系,前行为人不再承担逃逸致人死亡的责任。
合义务的替代行为在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中,主要是行为人逃逸之后,伤者被第三人救助但仍旧死亡的,逃逸行为与死亡结果同时具备,此时行为人是否需要承担逃逸致人死亡的责任。可以明确的一点是,行为人即使不逃逸死亡结果仍旧会发生,那么在此时,可以进行这样的理解,死亡结果并不是由逃逸所导致,而是先前的肇事行为已经酿成了一个无可避免的结果,只是结果定格在行为人逃逸之后。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致人死亡指的是,逃逸行为使本可以获救的被害人没有得到及时救助而死亡,与前述的因果关系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同时,从结果避免可能上来说,行为人虽能避免行为,但并不能避免结果,因此,也不能让行为人承担逃逸致人死亡的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行为人肇事以后逃逸导致第三人死亡的,也不属于逃逸致人死亡,因为这里的死亡结果仅与逃逸行为存在因果关系,而与基础的肇事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属于一个新的独立的因果关系,是一个新的交通肇事行为人,而不能评价为前一个肇事行为的延续,因而在这里,也不能认定行为构成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而是构成两个交通肇事罪,数罪并罚,这样从法益上和行为构成上都更为合理。

★
杨宜 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