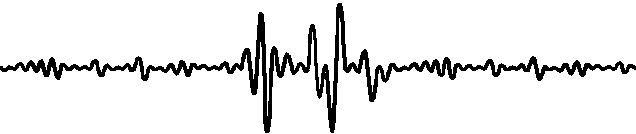聚会酒后驾车撞人,同饮者是否担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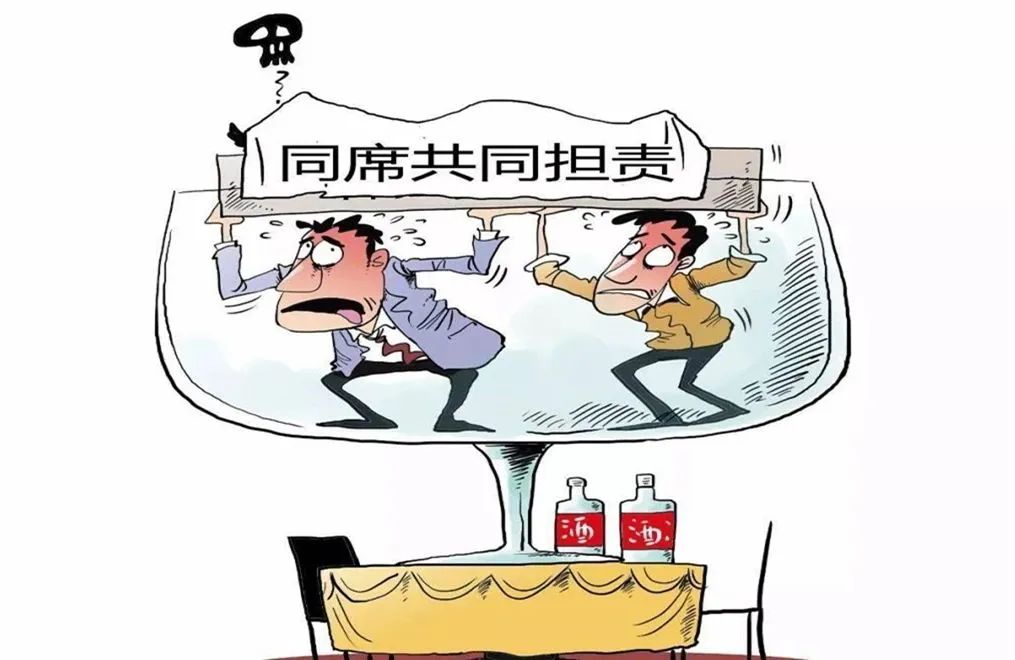
图片来源于网络 (侵删)
好友相聚,小酌几杯人之常情,饮酒过量则容易引发意外风险。宴饮当场或者回家途中发生醉酒者受伤害,召集人、宴饮参与人对醉酒人酒后致自己伤亡损害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新闻报道,偶有出现在日常生活视野。对于饮酒者酒后驾车撞伤他人,聚会组织者、参与者是否须向车祸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也是值得了解和关注的话题。
撰稿人:陈明前
一、同饮者间负阻止风险转化责任
(一)注意义务来源
聚会饮酒系亲友间情谊行为,属于好意施惠的事实行为,缺少产生法律上权利义务关系后果的意思表示。本身不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共饮人之间也不存在契约关系,但该事实行为因有外部人员主动参与或被动涉及,存在外部性,基于活动的外部性,因行为存在潜在危险而产生了安全注意义务,共饮者之间负有阻止损害发生的责任。
当生活情谊行为置他人处于危险状态,进而造成他人人身损害的,此时情谊行为转化为法律事实,产生了侵权法律关系。饮酒行为会使饮酒者神智、自控力明显下降,自我防护意识和防护能力降低显著,饮酒者在人身和财产上会处于比正常情况下更为危险的境地,从事驾驶等高度风险活动时,不安全系数明显增加,同时,也会置社会大众、公共秩序处于危险状态。此外,就同饮者的范围来说,不光包括共同饮酒的“酒友”,也包括仅参加聚会活动而没有喝酒的人。
(二)加重共饮人责任行为类型
宴饮结束后,未将醉酒者安全送回交由家人照料的,或者饮酒后出现紧急情况同饮者未能及时送医救治的,同饮者须承担相应责任;对于饮酒人酒后驾车行为未能有效劝阻,进而导致发生车祸事故等损害后果的,同饮者也须承担责任,其又乘坐酒驾者所驾驶车辆的,基于这层更紧密的关系状态考量,该类同饮者所承担责任比例会进一步加重。
其他行为也会加重同饮人的注意义务程度,比如宴饮时带了过量的酒,则会加重召集人的注意义务;聚会场地提供者在照料醉酒人时,不能擅自离开,明知醉酒者处于不安全的环境还是放任不管,发生危害后果的,也须承担相对较重的责任;强迫性劝酒,比如用“酒品看人品”“不喝看不起我不够朋友”之类的语言要挟刺激对方喝酒,有劝酒、斗酒、赌酒行为的同饮者须负担更重的赔偿责任。

二、同饮者赔偿担责与否案例解析
(一)同饮人、车辆共有人、同乘人身份重叠,责任承担
亲友聚餐常以家庭为单位,在聚会中饮酒并驾车搭载家人返回,此种情形配偶既是聚会活动参与者,又是车辆共有人、同乘人,返家途中酒后驾车撞伤他人,同乘配偶是否对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中国法院2021年度案例》,收录了安徽省岳西县人民法院(2019)皖0828民初2281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例,结合其他同类案件判决情况,解析探讨。
安徽省岳西县人民法院 (2019)皖0828民初2281号 | |
案情简介及分析 | 刘某娥清楚丈夫王某宏饭后需骑车回家,对丈夫的饮酒行为没有加以劝阻,且对丈夫酒后驾车也未予阻拦,甚至乘坐同一辆车回家。无论是出于宴饮活动参与者的提醒劝阻义务,还是车辆共有人的管理责任,亦或双方共同使用车辆通行的行为,刘某娥对损害的发生,过错都十分明显,判决认定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20%份额)。 余某胜作为宴饮活动组织者,没能妥当控制好宾客饮酒量,在王某宏酒后提出驾车返回时,其亦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阻止酒驾行为,不当履行先前行为带来的义务,对车祸造成的损害应按过错程度担责,考虑其对王某宏酒后驾车有过口头劝阻行为,过错程度相对较小,认定余某胜承担5%份额的赔偿责任。 |
裁判观点 | 夫妻共同财产所有人之一,对于另一共同所有人酒后驾车负有过错且双方共同乘用车辆出行,致第三人损害的,应负赔偿责任。 |
安徽省凤台县人民法院 (2017)皖0421民初2408号 | |
案情简介及分析 | 武某与徐某共同饮酒,后由武某开车送徐某回家途中碰撞路人,车祸造成一人当场死亡另一路人经抢救无效于两日后死亡的严重后果。同饮者徐某对武某醉酒驾车行为没有尽到制止义务,武某肇事后驾车逃离事故现场,徐某没有制止武某的逃逸行为,也没有采取报警及抢救伤者措施,而是任由武某将其送回家。 同饮者徐某,其放任行为对事故发生和损害后果的进一步扩大均存在一定过错;同时,武某义务送徐某回家,徐某亦系受益人。 |
裁判结果 | 由徐某承担20%事故赔偿责任,武某承担80%赔付责任。 |
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法院 公众号宣传案例 | |
案情简介及分析 | 2020年8月,康某与薛某、王某、刘某约好聚餐。饭后,薛某开车送三人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致驾驶电动车的徐某受伤致九级伤残,徐某对薛某等四人提起诉讼。薛某认为其酒后开车时,其他三人未劝阻,也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其他三人则认为自己对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不承担赔偿责任。 长清区法院审理认为,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各责任人应按其过错大小承担赔偿责任,徐某的损失,应先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对于超出交强险部分的损失,因事故发生在薛某、王某、康某、刘某共同饮酒后,且事发时王某、康某、刘某均在车内,三人作为“共同饮酒者”,对于薛某酒后驾驶行为未履行提醒、制止义务,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且三人又为无偿乘车受益方。 |
裁判结果 | 超出交强险部分的损失,由薛某承担70%赔偿责任,王某、康某、刘某各承担10%赔偿责任。 |
据胡岩教授2017年发表在国家法官学院主办期刊“法律适用(司法案例)”上题为“共同饮酒法律责任实证研究”的文章介绍,通过对142件涉及共同饮酒侵权案件判决结果梳理,共饮者担责案件占比共计达92.2%,也即同饮者被诉,超九成无法免责,详见下表:
142例共同饮酒侵权案件梳理 | ||
裁判观点 | 件数 | 比重 |
共同饮酒者在酒后负有注意义务,应承担赔偿责任 | 97例 | 68.3% |
裁判承认,同饮者不存在过错,但仍须按公平原则承担补偿责任 | 34例 | 23.9% |
驳回诉请,同饮者不承担责任 | 11例 | 7.8% |
(二)缺乏因果关系,不担责
侵权责任中的因果关系,分为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两类。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是指侵权行为事实上是否对损害发生具有原因力;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则指即使事实上因果关系成立,还要进一步判断义务人对损害发生是否具有可预见性,损害是否过于遥远,以至于义务人已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在数个事实因果关系中,与损害结果“最近”的行为,具有法律上的意义,就是法律因果关系。
安徽省黟县人民法院 (2020)皖1023民初238号 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皖10民终55号 | |
案情简介 | 陈某明邀请亲友汪某、胡某等八人聚餐,席间饮酒,饭局散场陈某明同胡某等五人移步他处玩了一个多小时,随后驾车回家途中碰撞路人致两人死亡,死者家属将所有参与聚会人员告上法庭。 |
裁判结果 | 黟县法院审理认为,没有证据证明席间有人劝陈某明饮酒,且饭后陈某明还同胡某等人到他处逗留一个多小时,损害发生与共同饮酒行为有较长时间间隔,汪某等八人参与聚会同饮行为与交通事故及损害结果无因果关系,同饮者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审宣判后,死者家属不服上诉至黄山中院,黄山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三、赔偿责任承担方式
(一)共同责任的承担形态
在合同之债、侵权之债等法律关系中,共同责任的承担形态有按份责任(又称“分割责任”,其中补充责任是按份责任的特殊类型)、连带责任(包括不真正连带)两大类,分别对应《民法典》第177条【按份责任】、第178条【连带责任】规定。按份责任是多数人(侵权)责任的常态;连带责任往往基于数个责任人的共同行为或者具有共有关系而产生,且连带责任往往会加重责任人的负担,法律对其适用有严格的要求,只有在法律有专门规定的情形下方可适用,即连带责任采法定主义原则。
就交通事故侵权行为,宴饮活动组织者、参与者、驾车人之间主观上没有意思联络,客观上也没有共同实施侵权行为,不成立共同侵权,不适用连带责任。共同侵权行为,指数人基于主观上的或者客观上的关联,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多数人侵权行为,既包括有意思联络的主观共同侵权,也包括客观行为共同侵权。组织者、参与者对醉酒者驾车可能发生的损害后果,应当且可以预见的是抽象的危险发生的可能性。醉酒者驾车过程中,面对可能引发交通事故发生的客观情况时,应当且可以预见的是可能发生的具体的危险结果,该危险结果是否发生,驾车人的认识因素(及时准确发现并正确进行判断)、意志因素(是否采取规避危险的措施)、行动因素(快速准确实施避险措施)起到关键作用。组织者、参与者与酒驾人的认识内容、范围不同,更谈不上有主观上的意思联络,不属于主观上共同侵权。同饮者的不作为行为相互是独立的,没有客观上的共同实施行为,也不属于客观上共同侵权,因此,多数同饮者侵权行为不构成共同侵权行为。
宴饮活动组织者、参与者对醉酒者驾车致人损害所承担的责任,也不符合补充责任成立条件,不适用补充责任。司法实践中有一定比例案例裁判说理中认为共饮人义务来源于安全保障义务,有主张同饮者责任适用《民法典》第1198条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承担补充责任。一般来说,群众性活动组织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与第三人侵权是相对独立的,当然第三人实施侵权往往利用了群众性活动安全保障上已经存在的漏洞这一条件,但该条件对第三人是否实施侵权行为并不发生开启流程的决定性的作用,在时空上不是分阶段的,而是重合或者包容的;在过程上不是演进,而是各自独立存在,没有结合成为一个整体行为,因此两者之间应当分开评价。而宴饮活动组织者、参与人和酒驾者之间,各自行为在过程上前后相继演进,在时空上分阶段,两者相结合构成一个整体行为,故不适用补充责任规则。
(二)典型数人分别侵权,各侵权人之间按份担责
共同饮酒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系典型分别侵权行为,属于因果关系聚合型数人侵权行为类型,活动组织者、参与者应按其过错和原因大小承担按份责任。根据每个人的侵权行为对造成损害原因力的大小,可将分别侵权行为分为叠加型分别侵权行为、半叠加型分别侵权行为以及典型的分别侵权行为三类。其中,在叠加型与半叠加型分别侵权行为中,至少有一个人的行为对损害的发生具有100% 的原因力,而典型分别侵权行为中,任何一个人的行为对损害的发生都不具有100% 的原因力。
叠加分别侵权 | 半叠加分别侵权 | 典型分别侵权 |
每个侵权人的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100%) | 有的人的行为足以造成全部损害(100%),其他人的行为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50%) | 每个侵权人的行为都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50%) |
100%+100%=100% | 100%+50%=100% | 50%+50%=100% |
在共饮人酒后驾车造成他人损害侵权案件中,共同侵权人的责任承担形式应为按份责任形态。在多数同饮人侵权行为中,尽管每个同饮人的不作为行为都是造成损害的原因之一,但是任何一个同饮人的不作为行为都不具有100%的原因力,每一个同饮人的不作为行为对损害发生的原因力都是介于0和100%之间,因此,多数同饮人侵权行为构成典型的分别侵权行为,不构成叠加型与半叠加型分别侵权行为。就各侵权人内部而言,在共同饮酒活动中,组织召集者、一般共饮人所处角色不同,新老朋友、亲属关系等亲疏关系不同,其所负注意义务程度也有所差异,其不作为所占原因力亦有所区别。
聚会组织者、参与者如能有效制止“酒友”酒后驾车行为,就能从根本上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未能有效阻止的,则是放任了潜在风险流向损害结果的转化。正是组织者、参与人和酒驾者各自行为前后相继演进,在时空上分阶段、在作用机理上互相依存互为媒介,相结合成一个动态的、演进的、完整的行为过程,最终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他们之间符合累积的多人侵权形态,也即因果关系上聚合性数人侵权。期间,召集人、参与人等共饮者的不作为在侵权行为开端阶段发生作用,但其过错、行为原因力在整个侵权行为中作用较弱;酒后驾车,系酒驾人自主决定,自行实施具体致害行为,驾车人自身过错和原因力在侵权行为中,所起作用更为主导和关键,依据《民法典》第1172条规定,应以过错及原因力大小、对整体侵权行为的作用,来确定酒驾者与其他共饮者之间相应的按份赔偿责任。
(三)同饮者担责比例,注意义务的合理边界,以及不担责或轻微责任情形
司法实践中,针对共同饮酒人承担侵权责任,裁判结果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各方共同承担责任。大部分情况是酒后驾车者承担主要责任,其他共同饮酒人依据责任大小按比例分担赔偿责任。二是基于公平原则。尽管饮酒行为本身并无不当,但为了维护社会和谐,判决各共同饮酒人给予受害者适当的经济补偿。
同饮者虽负有注意义务,但也不宜承担过重责任,以轻微责任为主,担责比例一般在5%-10%之间,显著轻微的在2%-3%之间;宴饮组织者作为召集、主导共同饮酒活动的人,对其他参与饮酒活动人负有更高注意义务;同乘人因具有更紧密关系状态,较一般参与者也应承担更多责任,召集者、同乘者承担责任比例一般在10%-20%之间。
类型 | 担责比例 |
显著轻微 | 2%-3% |
一般情况 | 5%-10% |
宴饮活动组织者、同乘人 | 10%-20% |
义务尽到。参与共同饮酒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基础,在于其未尽到应负有的注意义务,如果部分参与者已经完成了相应义务,那就没有承担责任的理由。此类情形包括:宴饮活动中未饮酒人在他人饮酒过程中适当提醒、劝阻,在酒宴散场后也进行照顾、护送醉酒人或者通知其家人,在其可预见范围内对饮酒人进行了妥善安置的;宴饮活动中,因故中途先行离场者,在饮酒过程中没有劝酒、拼酒、灌酒等不当行为,也提醒劝告各饮酒人适量饮酒,不负有阻止共同饮酒人酒后驾车不当行为及护送的法定义务,通常无需承担责任,(2018)川0722民初113号案中李某中途离场不承担赔偿责任即是佐证;初相识者在饮酒过程中没有强迫他人喝酒的不当行为,酒后亦无明显失当举动的;同饮至酒宴结束,同饮者尽到照料、通知义务,将其安全送回交由家人照料的;宴饮散场,劝阻饮酒者不酒后驾车,帮忙叫代驾并等候代驾人员到来搭载饮酒人离开的。
劝阻程度。劝阻须以有效性为标准,即使存在帮忙叫出租车、挽留等行为,但最终没能制止驾车行为的,可能仍需承担少部分责任。积极帮助饮酒者叫代驾,等候代驾人员到来待车辆离开后再离开更为稳妥,在饮酒者不听劝阻执意要驾车时,建议可采取控制其车辆钥匙、报警等方式加以强制制止。
因果关系中断。酒后驾车回到家中或由同饮人安全送回交由家人照料,后又因其他原因驾车外出造成自身或他人损害的,则由于因果关系的中断,同饮人不再负有责任。在(2017)苏06民终4260号【江苏高院再审案号:(2018)苏民申2900号】案件中,南通中院认为:饮酒者李源在驾车回到家后又外出发生交通事故致死,同饮者劝阻李源酒后驾车的义务与其死亡之间,并不存在侵权法律关系上的因果关系(即原因力),同饮者不再负有责任,该裁判意见在再审阶段得到了江苏高院的认可和维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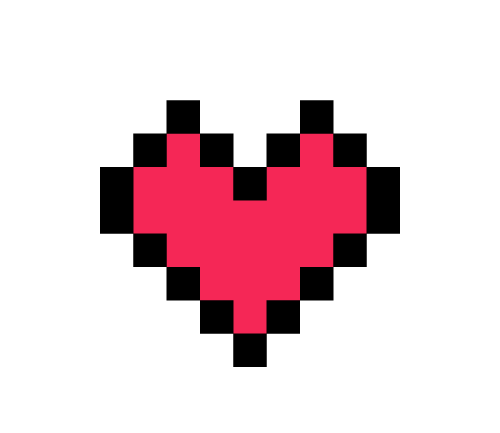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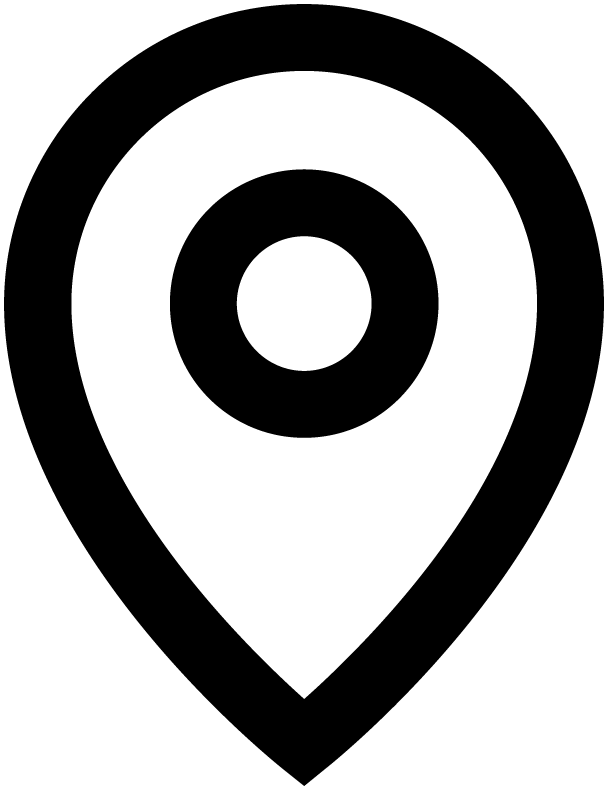
END
陈明前 18715515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