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TO MY MOTHER /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有时为了出行方便、节能环保,或者为了避免交通拥堵、停车难等问题,亲朋好友之间互相免费搭乘车的现象非常普遍。但在搭乘“顺风车”的过程中,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搭乘人遭受伤害,则被搭乘人出于善意的助人为乐行为往往会引发纠纷,甚至将面临大额的经济赔偿。
2020年5月通过的《民法典》第七编侵权责任中,新增了关于好意同乘减责条款,使善意被搭乘人减轻责任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在诸多学术论著与实践中,何为好意同乘,好意同乘致搭乘人损害时如何适用归责原则,怎样划分赔偿责任才能实现好意人善意与搭乘人利益保护的平衡,能否拓宽救济途径为好意人和搭乘人权益提供有利保障,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这些问题均存在争议和分歧。在《民法典》颁布施行的背景下,本文对好意同乘致损赔偿责任进行探析和建议,希望能为实际生活中纠纷的解决提供有益路径。

一、明确好意同乘相关法律规定
好意同乘认定标准的统一是有效解决好意同乘致损纠纷的前提。目前,我国法律并未对好意同乘的含义和认定标准做出明确规定,《民法典》第1217条也仅对好意同乘致损减责问题作出规定。明确好意同乘构成要件和主体能使司法裁判者准确把握其认定标准,依法适用好意同乘规则解决纠纷,也能让公民正确认识好意同乘行为,发挥法律指引作用。笔者认为将好意同乘的构成要件和主体限定加以法律明确规定,能为司法裁判提供细化的法律尺度,加强好意同乘致损赔偿制度的可操作性,从立法上遏制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发生。
二、完善赔偿责任归责原则
(一)排除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当下,对于好意同乘的归责原则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找不到明确的规定,司法实务中对于好意同乘致损归责原则适用莫衷一是。有观点提出,可以援引《道路安全法》第76条确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以便使搭乘人损害赔偿得到最大保障。但笔者认为该条文只考虑到对车辆以外的人员赔偿,却未考虑对车内的乘坐人赔偿,在搭乘人受损的情形下不能援引这一条作为我们论证的大前提,并且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下我们才可以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从无过错责任法理基础考虑,也不适用无过错责任。在好意同乘过程中,若发生事故好意人与搭乘人都将遭受相同的危险,好意人严格谨慎的驾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是为了他人的利益,且好意人也未以从搭乘人处获取利益为初衷,反而因好意行为还要多花去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在发生事故时,好意人车辆肯定也有损坏,甚至自己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受到损害,不问过错与否还须对搭乘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对于好意人来说显然有违公平,所以在无过错责任适用上既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也没有理由充分的实践依据。
也有学者认为西方国家的无过错责任原则还是有其合理性的,我们也可以进行借鉴,笔者对此持反对态度。我国的国情与西方国家是有很大不同的,在制度设计上也有很大差异,西方国家关于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赔偿范围是覆盖搭乘人的,所以当好意同乘造成搭乘人受损时,搭乘人首先应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但国内制度下适用无过错责任对于搭乘人保护是有欠缺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对保险赔付的范围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不包括司乘人),缩小保险的责任范围一方面加重了好意人需要承担的责任,另一方面受害人获得赔偿的途径也减少了。因此,我国采用无过错原则的前提是保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二)合理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是以行为人对损害发生在主观上存在过错与否作为判定其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从法律规范角度分析,好意同乘致损构成侵权受到《侵权责任法》规制,而过错责任原则是《侵权责任法》的一般原则,具有普适性,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时,应考虑适用过错责任。好意出行时好意人对搭乘人负有安全注意义务,发生交通事故致搭乘人损害时,适用过错责任不仅是为填补受害人遭受的损失,也是对好意人因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的过错的惩戒,又不会因适用无过错责任而过分加重好意人负担,防止边际行为缩减而打击到好意施惠的积极性。又如前文所述,《民法典》第1217条中“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中机动车一方,是指机动车相对于外部作为一个责任主体,涵盖了机动车内部所有人,即包含机动车所有者、驾驶人及同乘人员。而好意同乘致损是好意人对搭乘人承担责任问题,属于好意人与搭乘人内部之间的责任,应认定为一般侵权问题,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根据过错的程度划分,过错原则的责任承担主要有两种学说,分别是一般过失说和重大过失说。重大过失说强调,好意同乘的好意者对交通事故责任的承担以对事故的发生为重大过失为前提,若好意者只是一般过失是无需承担责任的。一般过失说强调,好意者不能因其好意施惠的行为就减轻其责任,好意者作为行为者仍需对其行为负责,尤其因“过失行为”给同乘者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害承担责任,对好意人过失的程度和其应承担责任的比例需结合具体案例具体分析。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任何人任何时候都须谨慎对待,不能因其初衷是行良善之举而减轻其注意义务,认为只有过失程度达到重大甚至是主观上存在故意才承担责任,这跟我国当前国情和社会核心价值观是不相符的。首先适用重大过失处理原则需要法律明确规定,在法律无明文规定时,应当适用一般的通行标准和原则。其次,行为人的法定注意义务必须依法履行,任何理由都不能抗辩和降低履行义务甚至不履行义务,所以好意人的法定注意义务是不得降低标准的,尽管好意人是出于好意。但是因为好意同乘是社会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互助行为,应给予鼓励和提倡,减轻好意人责任就是对好意人行为的最大鼓励。所以笔者认为应当采用一般过失论,并可以在好意人的责任承担上进行适当的减轻。从《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可以看出,该规定支持笔者认为采用一般过失说的观点,同时第1217条的“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规定,对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情形是不能够适用减轻责任的。

(三)适时引入过失相抵原则
过失相抵是综合考虑受害方与侵权方权益的原则,如果对事故的发生受害方也有过错,那根据受害方自身过错的大小可以按相应比例减少侵权方的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阐述了过失相抵原则的具体情形即被侵权人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根据前文对好意同乘行为在致害时搭乘人存在过失的情形,且出于及时有效化解好意人与搭乘人之间的利益纷争,笔者认为适用过失相抵是解决好意同乘致损纠纷的现实需要。但如何合理适用过失相抵原则关键是准确把握“过失相抵”中的过失大小认定,过失大小应结合双方的行为,通过过错比较来进行认定。好意同乘致损中,搭乘人过错主要表现在:(1)明知驾驶人存在超速、超载或酒后、无证驾驶等违规违法行为,仍然搭乘;(2)搭乘车辆时违规不系安全带等;(3)干扰、指挥违规驾驶等情形。因此,适用过失相抵原则需根据好意人与搭乘人过错大小对引起事故的发生作用大小进行综合考量,以平衡双方各自应担负的责任。
三、好意人过错类型认定
规范归责原则适用后,就需要对过错类型进行划分,民事侵权中过错的形态依据主观心态不同可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种。《民法典》对民事法律关系中的“过错”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解释,学术界对“过错”的理解主要有三种:主观过错、客观过错和主客观混合过错。主观过错主要是分析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具有故意或过失的心理态度,在行为人应承担责任的前提下分析主观过错才有意义;而客观过错是行为人只要实行了某种行为,造成了损害,且行为与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即构成过错,不问主观心理状态;主客观混合过错则要求主观上具有故意的心态,客观实行了侵害行为,造成实际损害,主客观之间形成统一,才认定为主客观混合过错。从好意同乘致损纠纷看,笔者认为:其过错认定应当采取客观过错的标准。因为好意人与搭乘人之间的搭乘行为本就是一种好意施惠,好意人的出发点本就是基于增进彼此情谊,其主观上对于事故的发生是持否定和避免的态度的,同时,好意人与搭乘人共同乘坐车辆出行,双方之间的利益是趋于高度一致的,好意人除了有义务保护搭乘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要对自己的安全负责。
机动车交通事故发生后,通常由交警部门对事故进行专业鉴定,作出事故责任认定,当事人只需对事故发生不存在故意和重大过失承担举证,这也说明机动车交通事故举证责任倒置。但由于机动车驾驶的特殊性,驾驶人很多时候难以回避机动车高速行使存在的风险,机动车一方难以证明其已经谨慎驾驶,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好意同乘事故侵权不同于一般的机动车事故侵权,好意同乘是出于助人为乐的利他行为,对好意人可以承担自证其无过错的责任将会打击好意人乐善好施、互帮互助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引导向善向上的良好社会价值观。因此,笔者认为应由搭乘人对驾驶人在驾驶过程中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进行证明。
好意人责任的承担不仅需要考虑其应尽的义务,而且还需判定其过错程度来进行综合考虑。好意同乘致损本质上是在公共道路上驾驶机动车发生的侵权事件,好意人通常是排斥损害结果的发生,主观上不是积极追求损害结果的,过失按程度又可划分为重大过失和一般过失。重大过失的判定标准是好意人没有尽到一个普通人对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就可认定为重大过失;若尽到一个普通人对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依然发生安全事故则是一般过失,若要求普通好意人达到专业人士的注意义务是强人所难。在好意同乘中,好意人基于善意邀请他人搭车或顺路接送他人。这种搭便车可以加深彼此之间的感情,是应积极倡导的文明行为,发生交通事故完全属于好意人意料之外的,笔者认为:适用过错原则只考虑重大过失的这种情况才比较合理,若考虑一般过失则对好意人来讲显失公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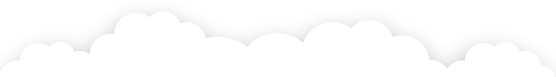

张 伟
188 5511 77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