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天刑事】诈骗罪专栏 | 诈骗罪虚构事实教义学研究

关注公众号并留言 免费咨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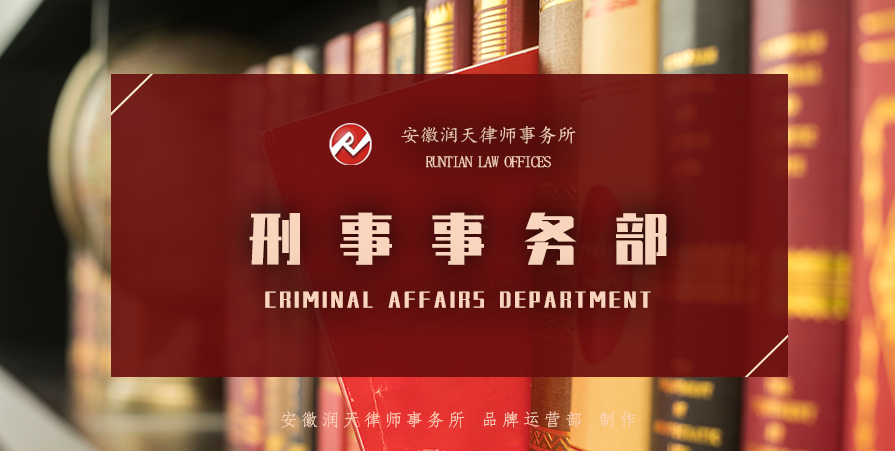
编者荐语
本文所讨论的对象是诈骗罪中“虚构事实”的事实,提倡从事实与价值上对虚构的内容进行区分,以区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论者认为事实描述与价值判断并不是完全统一、也不是完全相对的关系,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换,即当行为人为价值描述提供了客观的判断标准时,价值判断就成为虚构事实的具体内容和对象。当行为人对部分事实进行虚构时,从虚构的事实与主要事实的关联性程度、是否虚构新的事实上判断行为是构成诈骗还是民事欺诈。
来源:《北方法学》第15卷总第87期
作者:肖志珂 上海商学院商业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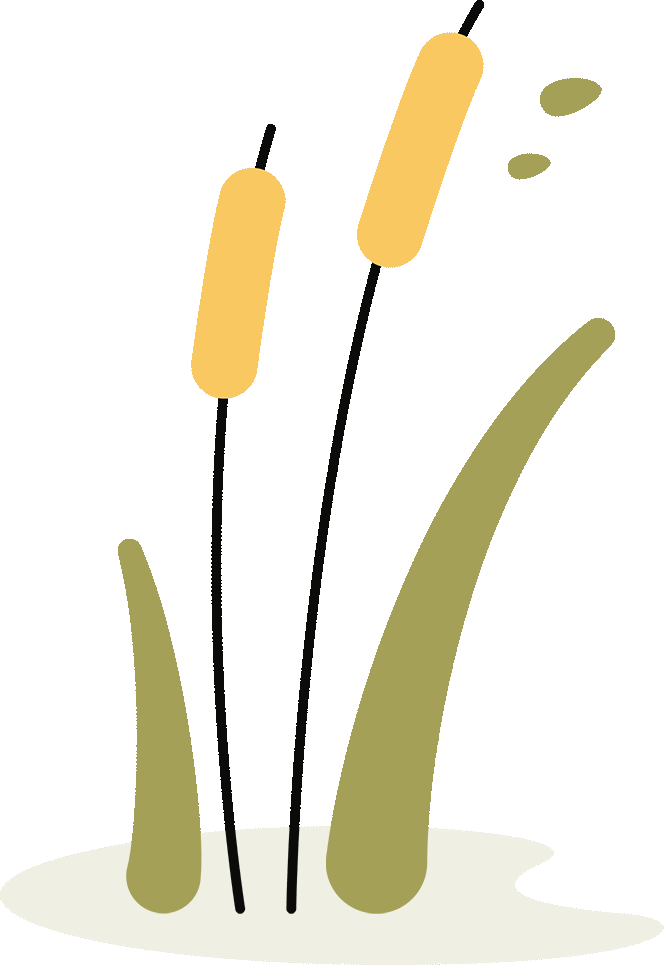
摘要:诈骗罪的欺诈行为包括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两种方式。从语义上看,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是欺诈行为的两个侧面,分别是指从无到有与从有到无的两种语义内涵。根据事实与价值二元论,事实描述与价值判断存在本质不同,需要对两者作出合理区分,以准确界定虚构事实的指称范围。虚构事实包括虚构全部事实与虚构部分事实,对部分事实虚构的理性认识,可以达到对刑民关系准确认识之目的,也是合理辨析刑事犯罪与民事侵权的重要标准。
关键词:诈骗罪 欺诈行为 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
从理论上看,对诈骗犯罪的关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非法占有目的、财物处分意识与处分行为等问题层面,以准确解读诈骗类犯罪构成的定性标准,并认真探讨诈骗犯罪与民事侵权的关系,以及诈骗犯罪与其他财产犯罪之间的界限。需要指出的是,理论界对诈骗罪欺骗行为的关注度远远不够,尤其是对诈骗行为的基本行为构造缺乏深度研究,致使理论上在适用诈骗类犯罪构成分析个案行为时,往往呈现出相对模糊且宽泛的界定和认识。在涉及虚构事实的范围界定时,往往习惯于将其与价值判断作简单区分,但何谓价值判断及其与事实描述之间应如何区分,并未给出合理的解答。鉴于诈骗行为与民事欺诈是刑法上的重要问题,也是疑难问题,因此,关于诈骗犯罪的行为构造研究,也是推进和发展合理认识刑民关系的关键所在。
一
提出问题
案例1:张某到按摩店按摩,按摩过程中服务员暗示,顾客升级为会员后可以享受色情按摩服务。顾客在办卡升级为会员后,按摩店并未提供色情按摩服务,还是普通的按摩服务。对以色情按摩服务为诱饵骗取财物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行为需要研究。按摩店并未提供暗示的色情按摩服务,实质上属于虚构事实行为。由于是在正规按摩基础上虚构色情按摩,行为人虚构的是部分事实,对此,是否可以认定为诈骗行为,是刑民关系认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案例2:行为人将一匹驽马称为“体格实在健壮之马”,使对方以为该马为骏马而高价购买。也即,将驽马声称为骏马而使他人高价购买的,是否应当认定为欺骗行为。一定程度上,驽马与骏马的区分属于价值判断问题,马的优良程度是从符合人实际需要角度进行讨论的,不只是对马的客观描述,而是对马的价值判断。问题是,行为人对马进行夸大的价值判断,并引诱其他人高价购买的行为,是否构成刑法上的诈骗行为。
案例3:行为人进入餐馆订餐食用,或进入旅社订房住宿,通常观念上,商家会认为食客或住宿人对于餐费或住宿费具有支付能力。故若食客或住宿人明知自己身无分文,根本无支付能力,但又去消费的,使商家依据通常观念而误认食客或住宿人有支付能力而供其食宿,至结账时却无钱可付,自可构成欺诈行为。但是,该欺诈行为是虚构事实还是隐瞒真相,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明确,而不应该做模糊认定和处理。
二
诈骗行为中的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
从我国刑法理论看,就诈骗罪的行为构造看,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是诈骗行为的两种情形。不过,很少有学者对隐瞒真相与虚构事实的行为构造进行深度研究,往往只对诈骗行为作整体性考察。在司法实践上,司法主体对诈骗行为一般也不作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具体区分和认定。
关于诈骗罪行为构造的规定,不同国家的刑事立法表述存在一定区别,总的来看,主要分为两种立法模式:一种是在诈骗罪立法条文中明确规定,诈骗行为有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两种情形,如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刑法条文关于诈骗罪的立法规定。《德国刑法典》第263条规定:出于使自己或第三人获取非法财产利益的目的,通过虚构事实或者通过歪曲、隐瞒真相引起或维持认识错误从而损害他人财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罚金。《意大利刑法典》第640条与第641条分别从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两个方面对诈骗罪的行为方式进行了规定。另一种是明确规定诈骗行为就是指欺骗他人的行为,但未作具体行为的类型区分,比如日本、美国、加拿大以及我国的刑法条文关于诈骗的立法规定。《日本刑法典》第336条规定:欺骗他人使之交付财物的,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加拿大刑事法典》第361条规定:欺诈是指以言辞或其他方式对过去或现在的事实作虚假陈述,行为人明知此陈述是虚假的,并怀有诱骗听取陈述人照此行事的目的。通过分析上述不同国家的立法模式可知,关于诈骗罪行为构成的立法方式存在一定区别:有的国家在刑法中规定诈骗行为包括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有的国家的刑法则规定欺诈行为就是虚假陈述,并未对其作进一步的区分。但是,通过分析不同的立法方式与刑法理论,尤其是主流的理论认识,可以发现,即使立法条文上没有对诈骗行为作明确区分,理论上关于诈骗罪行为构造的论述往往涵盖了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两种方式。因此,在对诈骗罪的行为构成进行分析时,需要从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两个维度进行展开。
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是规范的语言表达方式,为了达到对两者内涵的合理认知,就需要基于语义学,对两者的表达规律、内在解释、表达个性以及共性等方面有准确认识,以达到对词语内涵进行实然描述和应然分析之目的。总的来看,虽然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都是诈骗罪的行为构造,却是从不同侧面对欺骗行为内涵的概括和揭示。具言之,虚构事实是指行为人捏造并不存在的事实,骗取他人信任并处分财产。虚构的事实内容往往不是真实存在,是行为人为了骗取被害人信任而捏造的虚假事实。不过,有个问题需要明确,虚构事实是不是一个虚假命题?也即,既然事实都是客观存在的,虚构事实却是指向虚假的客观存在,这在语言逻辑上是不是矛盾的?从语言逻辑构造上看,事实是种概念,真实事实与虚假事实是属概念,都是客观事实的下位概念。由此,虚构事实也是一种客观实在,并不存在内在的逻辑矛盾。易言之,虚构事实是客观实在,只是虚构事实指向的具体内容并不存在。
在欺骗行为中,除了明示地陈述虚伪事实这样的“作为”之外,也存在负有告知义务的行为人不对被害人告知真实情况的“不作为”情形,这种情形就是隐瞒真相。隐瞒真相是指行为人负有告知义务却刻意掩盖客观存在的某种事实,以达到骗取被害人之目的。也即,某种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但行为人为了骗取被害人的信任而故意隐瞒该事实。具言之,从逻辑构造上看,隐瞒真相可以细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从小到大的隐瞒真相,即存在部分事实,依靠部分事实隐瞒并不存在的整体事实。具体如在合同诈骗罪的行为模式中,行为人没有实际履行合同的能力,却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另一种是从有到无的隐瞒真相,即存在某种客观事实,并对该事实负有说明的义务,行为人却刻意隐瞒该事实真相的行为。比如,《保险法》第16条第1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如果行为人本身患有某种疾病,却向保险公司隐瞒病情并投保健康险,以骗取保险公司保险金的行为,就属于欺诈行为的隐瞒真相。基于此,能清楚地看到,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是从两个不同侧面表述诈骗行为的文义内涵。也即,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的行为发生过程完全不同,前者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后者则主要是指从有到无的内容,但两者实质上都是诈骗罪行为的不法构造。但是,从行为发生过程看,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是完全不同的逻辑过程,对此需要有合理且明确的认识。
从语言结构与词语属性上看,虚构事实主要侧重于作为的行为方式,隐瞒真相主要表现为不作为的行为方式。基于此,对于实践当中发生的欺骗行为应该合理分析,以判断其属于虚构事实还是隐瞒真相。比如,《刑法》第196条第2款关于恶意透支行为的规定,根据恶意透支的内涵,行为人本来没有还款能力,也没有归还透支额度的意愿,却恶意透支信用卡进行消费,并向发卡金融机构虚构其会按时归还信用卡贷款的事实。由此,恶意透支信用卡的行为是一种虚构事实行为。对此,日本学者桥爪隆曾指出:“即便是使用信用卡购买了商品,既然在属于购买商品的要求行为这一点上并无不同,购买商品的要求行为本身就属于默示地显示付款意思或者付款能力的行为,应属于由举动实施的欺骗行为(举动欺骗)。”从教义学上看,行为人没有支付能力也不打算支付对价,却依然实施信用卡透支、餐馆消费、旅店住宿及加油站加油等行为,已经不再是民法意义上的债务不履行,而是通过自己的举动实施了欺诈性的行为事实,因此,可以构成欺骗行为。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行为人并未明示地表达,却通过自己的行为举止隐含地虚构或者歪曲了事实的,是默示的诈骗。笔者赞同论者的看法,前述行为属于默示诈骗行为,不过这种默示诈骗属于虚构事实还是隐瞒真相,在理论上还存在不同看法。对此,需基于语义学分析行为的发生过程,对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进行合理区分,就可以得出较为确定的答案。行为人没有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依然去饭店就餐,即行为人借助就餐习惯虚构出有支付能力的事实以欺骗饭店。易言之,行为人通过肢体语言虚构出有支付能力的事实,从而达到骗取财物的主观目的。对此,日本学者西田典之认为,一开始就没有支付的意思与能力,而在食堂点菜吃饭的行为,看上去是不作为的诈骗,但由于点菜时通常具有支付的意思,所以应当认为属于假装成有支付意思的样子的作为形式的诈骗。根据上文,国内有学者将该种欺骗方式称为默示型诈骗,也即虽不存在积极的虚假意思表述,但根据特定交易情境,从行为人的行为之中可推导出虚假意思表述。由此,这种默示型诈骗应该属于虚构事实。需要指出的是,不支付餐费并非诈骗行为的不法本质,如果据此将该种诈骗行为视为不作为的诈骗罪,显然是不合理的。
从学理上对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进行教义学上的区分,是为了对与两种行为模式相联系的不作为犯罪有合理、科学的认识。从实践上看,不作为的诈骗行为经常出现在行为人负有说明义务却故意隐瞒的场合。在关于社会福利的法律规定中,行为人在接受社会福利时,对客观事实变化的情况应该及时与政府部门沟通,否则就会因为违反说明义务而构成不作为的诈骗行为。对此,德国刑法学家Pawlik曾从自由理论出发,对真相义务进行了抽象而牵强的构造,将欺骗的本质视为真相义务的违反,认为诈骗罪的行为人具有真相义务或者说明义务这种保证人地位,违反之则成立诈骗罪,无论是以明示的方式,还是以默示抑或不作为的方式。对于学者Pawlik关于不作为诈骗罪的观点,有学者质疑该说不当地扩大了保证人地位的范围,混淆了诈骗罪作为与不作为的界限。笔者认为,这种质疑不无道理。根据Pawlik的观点,将欺骗的本质视为真相义务的违反,行为人具有真相义务或者说明义务这种保证人地位,于是将诈骗罪修正为义务犯类型,但是义务犯理论改造背离了诈骗罪的行为支配型的不法本质,从而在诈骗罪的行为认识方式上极易出现偏差。质言之,就隐瞒真相而言,行为人具有真相义务或者说明义务的保证人地位,即行为人负有真相说明义务却故意隐瞒,违背了法律上的不作为义务。不过,虚构事实违背的则是法律上的禁止义务,属于支配犯而非义务犯的范畴,正如顾客就餐、旅店住宿、加油站加油等行为,行为人虽然构成默示型欺骗,但不符合不作为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基于此,如果不能对诈骗罪的行为本质有合理认识,不能合理认识和解读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的关系,就会对与之相关的不作为犯罪有错误理解,从而不能准确界定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犯罪构成范围,以及与其相关的共同犯罪、犯罪形态等具体问题。
三
诈骗行为中的虚构事实与价值判断
在诈骗罪中的行为构成中,虚构事实的对象是编造的虚假事实。但是,在实践当中,如何理解虚构事实中的“事实”,如何区分虚构事实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关系,以及价值判断与虚构事实之间的转化等问题,还需要从教义学层面进行分析和论证。根据刑法对诈骗罪的规定,虚构事实可以构成欺骗行为,这在刑法理论上没有分歧,比如,各国刑法规定都明确指出虚构事实是诈骗罪的行为构造,但是价值判断并未涵盖在内。基于此,对与虚构事实关系密切的价值判断能否纳入诈骗行为范畴在理论上多持不同意见。日本学者植松正认为,只有对事实的欺骗才是诈骗罪中的欺骗,不可能就价值判断进行欺骗。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林东茂教授持相同观点:“至于价值判断,根本没有真假内容,无法凭着我们的认识能力去检验真伪,所以也不能欺骗。”甘添贵教授则持不同意见:“诈术之内容,无论系有关事实之表示,抑或有关价值判断或其他意见之表示,凡足以使人陷于错误者,均得成立诈欺罪。”对此,张明楷教授持折中观点:“就价值判断进行欺骗时,以存在一定的判断标准为前提。对于完全不存在判断标准的价值判断,不可能构成欺骗行为。”分析上述不同观点,肯定论与否定论相对偏颇,没有对价值判断在诈骗行为构成中的作用和地位进行辩证分析,结论的合理性不足。基于此,张明楷教授的折中论显得相对合理,但遗憾的是,折中论没有对价值判断的前提即判断标准进行具体化的分析,因此折中论看似合理,却可行性不足。
实践当中,股评人预测某只股票近期将会呈上涨势头,劝说投资人予以购买,并基于股票推荐向投资人收取咨询费用。但是,股票价格并未如股评人的预期上涨,而是不断下跌并导致投资人亏损。再如,房屋销售导购向购房人极力推荐某新开盘的房产,并预测房产价格会于近期上涨。购房人听从导购的劝告购买房产,购买后发现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下降,从而造成一定财产损失。基于此,行为人根据经济行情预测作出价值判断,并劝诱他人购买某种商品,却导致购买人亏损的行为,是否构成刑法上的欺骗行为,在理论上有不同观点。其实,要解决上述理论分歧,需要厘清两个基本问题:第一,需要辨析事实描述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关系,为合理区分事实描述与价值判断提供支持;第二,需要为价值判断提供客观标准,为价值判断转化为事实描述提供合理路径。
法律行为成立与否经常涉及事实描述与价值判断,这与近代以来哲学二元论的基本理论预设有关,最早源于英国哲学家休谟关于事实与价值的划分。休谟在《人性论》中指出,人们不能从“是”推导出“应该”,即纯事实的描述性说明凭其自身的力量只能引起或包含其他事实的描述性说明,而决不是做什么事情的标准、道德准则或规范。至此,休谟关于事实与价值二分的观点被后世作为基本的理论前提而接受。从哲学维度出发,事实是一种客观实在,是对事物的客观描述。基于逻辑学的知识,关于事实描述的命题有真假之分,这也构成了虚构事实行为的逻辑基础,也是判断事实真假的逻辑标准。与此对应,价值是客观事物对人类的用处或利益,反映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也即,价值是从应当或好坏等利益维度进行的考察和判断。由此,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其实是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维度展开的,是否符合人类的利益需要是区分事实与价值的基本标准。基于此,从理论上区分事实与价值是客观可行的。
自休谟提出事实知识与价值知识以来,理论上认为事实知识可由经验证明,有真假之分,而价值知识则不可经验证明,无真假之别,同时,从事实也推导不出价值,从而否定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联性、一致性。甚至直至新康德主义,休谟关于事实与价值的理论,还是新康德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者价值哲学的根据。不过,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事实与价值二分的理论预设逐渐发生改变,两者之间的关系日益被关注并联系起来。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至少是极为模糊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我们赖以决定什么是、什么不是一个事实的科学探究惯例,就已经预设了种种价值。”论者对价值与事实二分的观点提出质疑,并明确指出事实之身的价值色彩。对此,马斯洛明确指出:“是与应该的这种互相排斥的古老对立是虚假的对立,二者是完全可以贯通与统一的,即通过某种‘同时看到是和应该的’、‘统一的意识’来实现与应该的融合统一。根据西方哲学的发展维度可以做出以下基本判断:事实与价值的完全断裂不符合哲学相对论,但是将两者归结为完全贯通与统一,也违背了哲学相对论。”根据前述观点,对事实与价值的关系应辩证看待,二分论的观点欠缺合理性。在实质意义上,事实与价值二元论的关系是相对的,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并非是绝对的。质言之,价值本身也是一种客观存在,通过对价值赋予客观标准,价值也可以转化为客观实在。鉴于事实与价值二分的相对性,为实践上区分事实与价值带来一定难度。总的来看,关于事实与价值的认识可以从以下两个维度展开:
第一,应合理界分事实虚构与价值判断。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有真假之分;价值是主观判断,有好坏、当否之分。在实践当中,应该对事实虚构与价值判断做到合理认识。有个问题是,事实都是客观实在,虚假事实也是客观存在,那么,虚构事实是不是一个假命题。如果从哲学层面对事实本质予以理解,就不会混淆虚构的事实与虚构事实之间的关系。虚构事实就是虚构虚假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的事实。也即,虽然虚构的事实不是客观实在,但虚构事实本身是客观存在的行为。比如,算命人对被害人的未来命运进行预测,断定被害人将来会飞黄腾达,成为亿万富翁,并向被害人收取巨额的算命费用。对此,可能会有人提出,算命是对未来命运的预测,属于价值判断,没有办法检测真伪,不能构成诈骗罪上的欺骗行为。其实,对未来命运的预测,实质上并不是好或坏的价值判断,而是对未来的事实虚构。也即,算命人虚构了被害人未来成为亿万富翁的事实,是对其未来发展的一种事实虚构,因此,算命行为可以构成诈骗罪中的欺骗行为。第二,价值判断可以转化为事实描述。价值判断是对客观事物的利益性描述,鉴于每个人价值标准的差异,对价值判断很难得出真或假的认识结论。因此,纯粹的价值判断不应该成为欺骗行为。不过,理论上对该问题存在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没有必要区分是事实的描述还是价值的判断。有学者则认为,对价值判断进行欺骗的,也可以成立欺骗行为。张明楷教授曾指出:将驽马声称为骏马,使他人高价购买的,也应当认为属于诈骗罪中的欺骗行为。论者进一步指出,既然有驽马与骏马之分,就表明对马的优劣有评价标准,并不是任何马都属于驽马,也不是任何马都可以称为骏马。当行为人将驽马诈称为骏马时,便可以认定其对价值判断作出了虚伪表示。分析论者的观点,其实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可以对价值判断作虚假表示;第二层意思是,之所以可以作虚假的价值表述是因为有评价标准。实质上,论者是为价值判断的虚假表述附加了客观的事实表示,从而为价值判断是否能成为虚假表述的欺诈行为构建了判断标准。对此,笔者认为,论者的观点是合理的,遗憾的是,没有就如何为价值表述构建合理的判断标准给出可行性建议。
其实,当从理论上为价值判断提供客观性的事实标准时,一定程度上,在欺骗行为的构成上已经发生了转化。也即,行为人不再是对价值判断的虚假陈述,而是对客观事实标准的虚假构建,因为其虚构的是可以验证价值判断的客观事实,因此,就符合了诈骗行为的不法构造。比如,植松正教授曾指出:行为人将一匹驽马声称为“体格实在健壮之马”,使对方以为该马为骏马而高价购买的,并不构成诈骗罪。但如果谎称“该马去年在东京赛马时取得冠军”,使人信以为真,高价购买,则成立诈骗罪。根据论者的观点,“该马去年在东京赛马时取得冠军”,就是对骏马这一价值判断的事实支持,从而使得价值判断转化为事实虚构。对此,德国联邦法院也有判例持类似观点:单纯声称股票会升值的,尚属于价值判断,但是,谎称上市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并基于此声称公司股票会升值的,构成就事实的诈骗。国内也有学者指出,商业广告对产品功效进行了夸张宣传的,原则上并不成立诈骗罪;如果行为人声称该产品功效系经科学实验证明了的,则超出了单纯的价值判断或主观看法的范畴,应当成立诈骗罪。德国判例与上述论者观点无疑具有启发性,但是如果只是泛泛地声称上市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或者产品功效经科学实验证明,行为人并未提供更加实质性的证明,且不能足以使人陷入认识错误的,就不能成为检验价值判断的事实标准。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一般商品交易均允许存在一定程度的讨价还价与夸张,要构成诈骗行为,就必须是在以交易对方的知识、经验为基准的情况下,虚构足以使得一般人陷入错误的事实。”否则,就会导致刑事诈骗与民事欺诈的关系构成牵连,单纯的价值判断或表述容易被认定为诈骗行为。具言之,行为人在价值判断中需要包含可以验证的事实内容,该事实内容属于价值叙述的实质性证明,且该事实可以使一般人陷入认识错误,而并非行为人泛泛的事实宣称或者声明。
如果要从价值判断推导出事实描述,就需要对价值判断构建客观标准,标准构建需要根据价值分类而所有不同,也即,应该根据社会主体的需要、欲望、目的、利益等主观内容,构建符合主观需要的判断标准。正如布莱克教授所言:“事实如何的前提与应该如何的结论之间有一断裂,连接这一断裂的桥梁只能是当事人从事相关活动或实践的意愿。”详言之,如果具有国家标准、地区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这些标准就是价值判断的依据。如果具有科学实证依据的,科学实证依据就是价值判断的标准依据。如果需要根据一般人的认识进行判断,则一般人的客观认识就是判断标准。也即,在对事实描述与价值判断进行区分时,除了可以验证的事实,也可以纳入法定标准、社会观念、通常认知等外在要素。由此,如果行为人对价值表述作虚假描述,并根据相应的事实标准为其价值表述提供支撑的,这时候行为人不再是作价值判断,而是在进行事实描述,如果是在作虚假事实描述的话,则可以构成诈骗罪的虚构事实行为。质言之,事实描述和价值判断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发生转化,即当行为人为价值描述提供了客观判断标准时,价值判断就成为虚构事实的具体内容和对象。
四
诈骗行为中的整体虚构事实与部分虚构事实
诈骗行为中虚构事实包括整体虚构事实和部分虚构事实。整体虚构事实的诈骗是指,行为人描述的事实都是虚假的,并以此获取被害人的信任;部分虚构事实则是,行为人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虚构了部分虚假事实。整体虚构事实容易认定,部分虚构事实构成刑事诈骗还是民事欺诈,在理论上与实践上有不同看法,需要给予认真研究。
虚构事实的本意是行为人捏造不存在的事实,从而获取被害人的信任并使其处分财产。从实践上看,整体虚构事实的情况相对普遍,也是诈骗行为的基本行为方式,在刑法理论与司法认定上一般不存在疑问。比如,司法实践上的电信诈骗、网络诈骗案件一般都是整体虚构事实,行为人编造的各种事实基本都是虚假的,对类似行为的诈骗定性不存在困难。但是,对部分虚构事实行为则需引起理论关注,因其往往会涉及刑民关系的认定问题。就部分虚构事实而言,往往是虚构事实与客观事实并存,从而给诈骗行为的司法认定带来难度。也即,由于存在刑民交叉问题,因此,能否对部分的虚构事实认定为诈骗行为并非都是确定无疑的。部分虚构事实的诈骗是在客观事实基础上编造部分事实,以骗取对方的认可及财产处分,从而获取非法利益。鉴于部分虚构事实往往与客观事实有关联、重合或交叉的关系,那么如何认识既定的客观事实与部分虚构事实之间的关系,部分虚构事实是否影响到诈骗行为的司法认定,则需要从理论层面进行精细化和教义学研究。
部分虚构事实实质上是一个刑民关系问题,行为人虚构部分事实进行欺骗并获取不法利益的,构成刑事诈骗还是民事欺诈是理论上的争议问题,也是司法实践上的疑难问题。比如,在房屋装修合同当中,合同双方约定使用某种高端品牌的装修材料。但是在装修过程中,行为人却用部分低端品牌的装修材料替代约定的高端的装修材料,从而获取更多的非法利益。其实,房屋装修过程中的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就是行为人对被害人做出的部分虚构事实行为,属于房屋装修欺诈问题。那么,对于实践上装修合同欺诈问题是否应纳入刑法规制范围,理论上往往持否定的观点。对此,陈兴良教授就认为:“在诈骗罪的认定中,如果是以交易形式进行的诈骗,则该交易内容是虚假的,应当予以戳穿。如果该交易内容是真实的,即使在交易过程中存在民事欺诈,也不构成诈骗罪。”据此,如果交易内容是真实的,即使存在部分欺诈行为,也不能构成诈骗罪。除此,对于刑事诈骗和民事欺诈的区分,刑法理论上一般认为,还需要判断行为人的主观层面,即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诈骗犯罪与民事欺诈客观上往往存在重合,即行为人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难以从欺骗内容、欺骗程度等方面进行‘量’的区分,必须从非法占有目的上进行‘质’的把握。”为了有效分析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论者提出对象衡量说。根据对象衡量说,主要是从对价的充分性与对价的相当性两个维度,判断行为人提供的对价与其所获财物是否价值相当,并最终得出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结论。一定程度上,论者构建的非法占有目的证明标准是合理的,对合理辨析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具有积极意义。不过遗憾的是,关于对价的充分性与相当性应如何理解,论者并未给出明确的标准和建议。质言之,论者构建的对价衡量标准,由于相对抽象和模糊,而合理性不足,并不能为实践上判断非法占有目的提供充分、有效的理论支持。但必须指出的是,论者构建的对象衡量说这一界分标准,为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提供了一种创新性思路,为理论上深化探讨规范的问题解决机制提供了合理借鉴。
从部分虚构事实的行为结构来看,可以分为基本事实与虚构事实两个部分。根据基本事实与虚构事实之间的关系,判断虚构行为是构成刑事诈骗还是民事欺诈,应该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考察:第一,基本事实与虚构事实有密切关联。虚构事实是否改变了基本事实的性质,如果没有实质改变就属于民事欺诈,如果有实质改变就是刑事诈骗。比如,在人身伤害的保险事故中,行为人只是构成轻伤,却向保险公司报告是重伤,或者伪造人身伤害鉴定结论,就是改变了基本行为的性质,应该认定诈骗行为而非民事欺诈。相反,如果行为人只是夸大了轻伤的严重程度,比如改变轻伤的级别,由于没有改变基本事实的性质,只是夸大基本事实的程度,因此不构成刑事诈骗而属于民事欺诈。再如,在房屋装修过程中,如果行为人违背约定,全部或大部分使用低端装修材料,则属于改变基本事实,应该构成刑事诈骗;相反,如果只是小部分使用低端装修材料,由于没有改变基本事实的性质,则应该属于民事欺诈。第二,基本事实与虚构事实没有关联。需要考察基本事实与虚构事实之间的关系,即行为人虚构的事实是否属于新的事实,如果属于基本事实构成则是民事欺诈,如果属于新的事实则是刑事诈骗。比如,在最近出现的“套路嫖”案件中,按摩店的业务范围本来是正规、合法的保健按摩、运动按摩和医疗按摩等种类,但在经营当中,按摩师或店员劝说顾客增加新的按摩种类,如色情按摩或服务等,由于色情按摩不属于正规的按摩事项,因此如果行为人以此为由骗取顾客办卡消费,却最终提供正规按摩而不是色情服务的,则属于虚构新的事实,应该构成诈骗行为。不过,如果行为人只是劝说顾客提升正规按摩的等级,或延长按摩的时间,由于没有涉及到新的事实,还是属于基本事实的范畴,即使在实施过程中有一定的欺骗行为,如按摩的要求或时间未达到合同约定,只能构成民事欺诈行为。第三,基本事实与虚构事实有一定联系。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分析虚构事实是不是基本事实,如果是基本事实则符合诈骗的行为构成,如果不是基本事实则属于民事欺诈行为。比如,在贷款诈骗罪等犯罪类型中,行为人虚构的应该是贷款主体、担保合同、贷款数额等基本事实。如果虚构贷款主体、担保合同等基本事实的,能明确反映出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应该构成诈骗行为。但是,如果行为人提供的贷款材料中,部分材料不够真实,比如流水账单不全、单位地址有误、贷款日期错误等属于非基本事实的,并不能客观表征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因此应该构成民事违约。
五
诈骗行为构造中的虚构事实与处分事实
诈骗罪的行为构造包括两个基本的行为构成,分别为行为人的虚构事实与被害人的处分事实。如何从理论上认识虚构事实与处分事实之间的关系,对诈骗罪的犯罪构成、犯罪形态、共同犯罪等具体问题有实质影响,因此需要从理论层面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具体分析,以达到准确认识诈骗罪的目的。
从虚构事实与处分事实之间的关系看,虚构事实是基础事实,处分事实是关键事实。也即,虚构事实是诈骗行为的基础,处分事实则是诈骗行为的关键。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虚构的内容必须属于‘判断是否交付的重要基础事项’。要被评价为‘重要事项’,当然必须存在交付行为人本人如果没有就该事项陷入错误就不会交付财物或者利益这种关系。”由此,虚构事实作为重要基础事项,对处分行为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主流理论,诈骗罪既遂需要符合两个基本条件,即行为人的虚构行为与被害人的处分行为。在实践当中,可能会发生的问题是,行为人实施了虚构行为,诈骗对象却未实施财物处分行为,因此不符合诈骗罪既遂形态的犯罪构成,行为人只能构成诈骗罪的未遂形态。不过,有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是,理论上对财物处分行为应该如何认定,也即财物处分行为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在实践当中,经常发生的财产处分行为是,被害人将钱转到行为人的账户上或者将物交给行为人,这两种情况通常比较容易认定,即可以构成诈骗罪犯罪的既遂形态。不过,实践上还有些行为是不是构成财产处分还存有疑问:
第一,顾客没有将财物交给商家,而是交给第三方。商家业务员编造虚假事实,利用发行虚假广告欺骗顾客购买公司的产品,顾客因相信商家的虚假表述,而购买公司商品或服务,并将钱款转到公司账户上。质言之,商家为推销商品或提供服务进行虚假事实捏造和宣传,并导致被害人购买商品和处分财产。但是,鉴于获取非法利益的是商家而非业务员,不符合诈骗罪的犯罪主体要件,因此顾客的钱款转移行为不是诈骗罪中的财产处分行为。易言之,商家有虚构事实行为,被害人有处分行为,但并不符合诈骗罪的犯罪主体要件。根据具体的行为方式和犯罪构成,应该构成虚假广告罪或者商业欺诈行为。第二,商家让顾客办卡消费,而非直接处分财物。商店店主通过虚构服务项目劝说顾客充值办卡,顾客相信商家店主编造的事实,并办理充值消费卡。在这个过程中,商家有虚构事实的行为,顾客也将钱款转入消费卡中,顾客办理消费卡的行为是否属于财产处分行为?其实,顾客办理消费卡的行为并未实际完成财产权利的转移,只有顾客进行实际消费,且商家从消费卡中扣除相应钱款之后,才能构成财产处分行为。换言之,虽然顾客将钱款充入消费卡中,但并未实际完成财产权利的转移,只是在商家与顾客之间构建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充值卡本身不是债权,而只是一种债权凭证,只有每次消费后结账时才属于对财产的处分,并未排除他人占有。”因此,顾客办理消费卡并充值的行为不是财产处分行为。第三,行为对象将财物交付行为人,但并不是基于错误认识。从因果关系的维度,虚构事实是诈骗罪的原因行为,处分事实是诈骗罪的结果行为。由此,在诈骗罪的行为构造中,虚构行为是处分事实的充分但非必要条件。也就是说,虚构事实只是诈骗行为的开始,被害人是否因为行为人虚构事实而实施财产处分行为,还存在不同情况。从实践上看,行为人实施了虚构事实的行为,但行为对象并未相信行为人虚构的事实,只是出于其他原因交付财物。比如,路人明明知道乞讨者有欺骗行为,但出于道义上的考虑,依然给其一定的钱物;再如,明知行为人是编造事实进行欺骗,但基于其他原因的考虑,仍然向行为人支付一定财物。对于上述行为,行为人虚构事实的行为,不是行为对象进行财产处分行为的必要条件,也即行为对象的财产处分行为不是因为虚构事实而实施的。由于切断了虚构事实与处分事实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行为人只能构成诈骗罪的未遂形态。正如有学者所言:“虽然存在以使之实施处分行为为目的的诈骗行为,但对方未陷入错误,而是出于其他理由交付了财物,则由于切断了诈骗罪所预定的因果关系,而限于成立未遂犯。”
还有个问题值得关注,当财物所有人或占有人处分财物时,如何判断其是否因为行为人的虚构事实而实施的处分行为。对此,我们认为,对于一般的诈骗行为而言,可以从社会一般人认识能力的角度进行考察,即客观标准。即如果社会中一般人都能对行为人的虚构事实有明确认知,则不能认为行为人的财产交付属于财产处分行为。但是,对于行业性、技术性强的事实虚构行为,则需从行为对象的角度进行主观判断,即需根据财物所有人或占有人的认识能力进行判断,进而决定其财产交付行为是否属于财产处分行为,即主观标准。因此,在财产处分行为的判断标准上,应该采取主观与客观并存的双重模式,采取双重的判断模式对判断财产处分行为相对科学、合理、有效,可以对不同的情况进行相对准确的判断,有利于诈骗罪犯罪形态的合理认定。
六
几个案例的回应
第一个案例中的“套路嫖”问题,鉴于行为人虚构了新的事实,即编造了为顾客提供色情服务的事实,并致使被害人处分了财产,因此,应该构成诈骗行为。第二个案例中的“驽马”问题,行为人编造的是价值判断而非客观事实,并且没有给出价值判断的事实标准,因此,与诈骗构造中的虚构事实并不一致,不能构成诈骗行为。第三个案例中的“霸王餐”问题,由于行为人没有能力支付、也不愿支付餐费,却给人支付餐费的假象,并吃“霸王餐”的行为,属于从无到有的虚构事实行为,即吃“霸王餐”构成欺诈行为中的事实虚构。
★
杨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