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天刑事】诈骗罪专栏 | 财产损失的认定规则和判断路径——以骗补型诈骗罪为视角

关注公众号并留言 免费咨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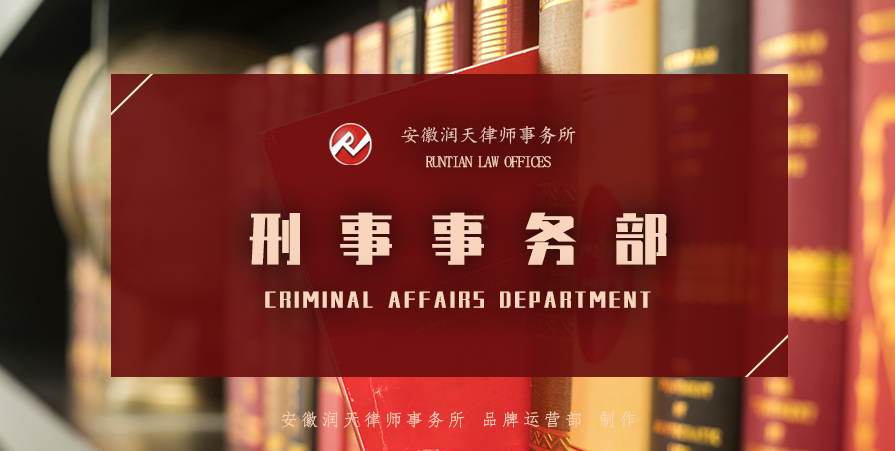
编者荐语
本文以骗补型诈骗这一诈骗类型为视角,介绍如何认定诈骗罪中的财产损失。文章未局限于经济的财产说或法律、财产的经济说之分,而是参照德国整体财产说,在单方给付的情形中,将经济、社会目的一并作为衡量实质的经济损害是否成就的标准,主张判断参与经济交换时比较财产是否收支合理、显失公平的客观的经济衡量方法,并借助社会惯常的使用目的和规律衡量目的是否落空来限缩处罚范围。
来源:《国际公关》2022年4月
作者:朱叶雯 华东政法大学
财产损失的认定规则和判断路径
——以骗补型诈骗罪为视角
摘要:区别于纯粹的以交易形式为载体的诈骗罪,以捐赠、骗补类诈骗为例的单方给付类诈骗以及混合交易类诈骗目前处于司法实务中解决难、争议大的困境中。虽然实践中对于诈骗罪的认定往往集中于财产概念的辨析以及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方法问题,但是财产损失要件在特殊类型的诈骗罪中作为判断诈骗罪罪与非罪的认定环节具有更为显著的研究价值和实用价值。本文尝试引入被害人目的落空理论从路径层面补充完善判断骗补类型的诈骗罪中的财产损失要件,结合案例指导制度,建构出多层次的认定路径。
关键词:财产损失;骗补类诈骗;目的落空理论;法律的财产说
一
问题的提出
农民异地购买农用机享受补贴案是典型的骗补类“诈骗”,案件源于国家财政针对农民购买农用机设置了专项补贴出发,补贴发放的对象和范围由财政部门预先设定且实施过程中不得变更。然而国家宏观设置并未真正起到因地制宜的效果,导致了农民异地甚至利用其他省市指标购买农用机享受补贴的情况。具体情形即某地农民没有实际对于农用机的需求,但是仍然虚构了需要购机的事实,获取本地政府的补贴,再将补贴出卖给其他地区的农民甚至经销商,自己则获得额外的利润。
该案件的复杂性不仅局限于骗补类诈骗罪构成要件层面的讨论,也涵盖了刑法的谦抑性、预防必要性及国家财政与实际需求的不协调等刑事政策相关问题,但本文将着重探讨财产损失要件在单方给付的骗取补贴类案件中的司法定位与判断路径的建构。
二
财产损失的判断路径
在诈骗案件中,财产损失作为客观构成要件层面的最后步骤,是在其他要件齐全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功能的。因此不能过度放宽财产损失的范围,厘清财产损失在骗补类诈骗中的判断路径是解决此类案件处理难的实务问题的关键。
01
经济的财产说与法律、经济的财产说
诈骗罪的范畴下,我国学界对于财产法益的定义存在法律的财产说、经济的财产说和法律的、经济的财产说。其中法律的、经济的财产说和经济的财产说是目前多为适用的理论。纯粹的经济的财产说注重金钱价值的衡量,对于盗窃罪、抢劫罪等单纯的侵财犯罪来说具有实用价值,“计赃论罪”的方式也与我国财产犯罪的实践中常以犯罪数额作为定罪门槛以及衡量罪刑轻重的标准不谋而合,然而经济的财产说给实务遗留了极大的缺口即无法精确地计算价值的物品如何计赃论罪。对于捐赠和骗取补贴类诈骗行为而言,没有对待给付的单方给付无法准确认定其金钱价值的流失,因此经济的财产说无法涵摄只有一方给付的诈骗罪中无法计赃论罪的情形。
法律、经济的财产说则主张被法秩序保护的有经济价值的任何利益都属于财产,物或利益应当兼具经济价值以及法秩序保护的必要性。在骗补类诈骗案件中,法律的、经济的财产说并不能通过其背后的法秩序保护进行规制。很难将“政府的农用机购买补贴资格”等同于不法原因给付。基于侵犯了被害人的合同自由意志为由,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诈骗罪,会导致诈骗罪的犯罪对象无限扩张,造成对于诈骗罪保护法益的曲解,同时也会助长该说本就被学者诟病的过分扩大犯罪圈的缺陷。
02
刑民范畴下财产损失的概念区分
目前我国刑法中并未将“造成财产损失”规定为成文的构成要件,但在立法和司法各个环节,衡量财产犯罪时将犯罪数额作为定罪与量刑的主要依据。被害人财产上的损失是许多财产犯罪的入罪门槛,“财产损失”要件也是司法实践中判断犯罪是否既遂的要件。
在学理的范畴下,准确界定财产损失的概念范畴必须区分刑法和民法在财产损失的保护立场的区别。民法赋予受损失方救济的途径主要包括不当得利返还、恢复原状、损害赔偿等,可见其规制目的旨在保护受损失方的利益,以达到“物归原主”的状态。而刑法中设置诈骗罪等财产犯罪的目的,通过衡量财产损失是为了确定其罪性及罪量,以期对不法获利者进行惩罚和制裁。根据刑法和民法的规制目的界分,应当明确的是财产损失的定义在刑法领域应当进行适当地扩张。
在判断诈骗罪尤其是单方给付的诈骗罪时必须准确界定“财产损失”的概念。根据所有权说考量是否存在财产损失完全忽略了法益侵害的确证,因此所有权说的式微是理所当然的。更好的做法是参照德国以整体财产说为纲,在单方给付的特定情形下,将经济、社会目的一并作为衡量实质的经济损害是否成就的标准。
03
客观经济衡量原则的适用
基于财产犯罪的处罚模式和财产概念日益复杂化的原因,目前学界关注的问题已经由财物性质问题转化为了经济运作和刑法规制的平衡问题。财产背后的财产利益的明确以及财产的利用或交换价值的衡量才是有形的财物外真正需要重视的概念。因此部分学者认为争论应采用日本的个别财产定义还是德国的整体财产定义并无实际意义,在财产损失的实务解决上,采取实质判断还是形式判断是司法实务突破难题的试金石。客观的经济衡量更为适宜我国交易方式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在对诈骗罪的损害结果进行客观的经济衡量时强调不能过分倚重金钱价值,客观分析损失的可罚性以及损失的数额。不论财产损失方是国家机关还是个人,只要通过其参与经济交换时比较财产是否收支合理,是否“显失公平”。此种客观的经济衡量的意义在于一旦财产的反对给付补偿了财产的流出,一般不构成财产损失。客观的经济衡量不仅符合刑法的安定性和明确性的要求,同时在诈骗案件的损失认定中也发挥着高效的判断标准的作用。对于单方给付的诈骗罪而言,客观的经济衡量可以提供给付方超越单纯的经济损失的保护,以适当扩大财产损失的外延。
三
骗补类诈骗中财产损失要件的认定困境
01
司法认定的现状与缺陷
在司法实践中,整体上对于诈骗罪的态度是审慎的。财产损失的统一的判断标准,特别是只有一方行为人提供给付,或在给付时从未期待反对给付时,如何确定财产损失不仅要引入客观的经济衡量的规则,同时也必须解决两大误区即认定财产损失的时间点以及无意识的自我损害的观念。当提供补助或捐赠时,财产提供者在订立合同时或者说在制定补助规则时就事前认识到自己不会获得反对给付,若以将财产的交付作为财产损失的认定时间点或以有意识的自我损害进行辩驳,那么该类诈骗行为完全可以规避刑事制裁的范畴。
02
无意识的自我损害考量必要性
在单方给付的情形中,给付财物的一方所设定的目的是否实现作为价值判断的依据,对于财产损失的认定具有弥补性的功能和关键的意义。
在讨论具体个罪是否成就之前,必须对于骗补类诈骗罪的受害人提供财物时是否必须出于无意识的自我损害进行探讨。无意识的自我损害即诈骗罪的被害人或者三角诈骗中的被诈骗者虽然认识到了自己对于财物的交付行为,但是由于陷入了错误认识因此交付财物时没有意识到自己或财物的实际享有者会遭受财产损失。虽然也有学者提出,社会目的的追求不应影响损失意识的认定,行为人是否有意识应当在确定存在财产损失后作为计算财产损失的范畴,显然这并不是目的理论适用的思路。无意识的自我损害应当是被诈骗者的交付行为的免责事项,是民事欺诈与诈骗罪的界分原因,并不是目的落空理论意图解决的范畴。
03
财产使用价值的规范化适用
“财产损失”是我国学界在财产犯罪中认定法益侵害的外在征表,不论是在捐赠案件还是在骗取国家补贴类案件中,单方给付的交易中,提供财产给付的一方因为期待其他目的的实现而容忍了整体财产上的减少,在缺少对待给付的案件中无法通过财产客观的金钱价值的衡量进行罪与非罪的确定。此时,我们可以通过引入财产的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作为规范化的价值判断方法。
在骗取补贴的情况下,客观的经济衡量标准无法作为准确界定财产损失,必须通过主观上受损失方的目的是否落空即被骗人针对特定财产的使用价值是否实现作为确定是否存在实际的损失的路径。例如日本学界提出的“可罚的利用妨害意思”则明确地指出了刑法中的财产损失在交换价值之外还包括使用价值,通过判断行为人是否侵害了被害人对特定化的财产的利用意思作为界定财产损失的方法,同时以“可罚”作为前置的限定。在符合罪刑法定的前提,也恪守了刑法的规制范围不会无限扩张。
四
目的落空理论的引入和适用
01
目的落空理论的规则述评
既然运用客观的经济衡量标准无法明确其财产损失,那么只能通过蕴含在财产损失之下的目的是否达成作为入罪的依据。在农民异地购买农用机享受补贴案件中,如果农民出卖农用机补贴是在已经拥有农用机的状况下,转卖给需要补贴的异地农民,那么财政设定的特定社会目的“恰好”实现时,已经例外性地阻却了财产损失的产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德国学界首先提出了目的落空理论,以适当扩张诈骗罪的处罚范围。为了避免矫枉过正,导致诈骗罪的限度无限扩张,也必须明确地界定“目的”与“目的落空”的定义和适用范围。根据该理论,即使存在相当的反对给付,不能直接得出不存在财产损失的结论,应当权衡被害人的重大处分目的是否达成,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实现。不过,财产损失作为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中征表了法益侵害的要件,即使将个人化的目的包含在考量中,也应当是客观的判断标准,而不能仅以被害人的主观目的为依据,对于目的的界定应制定一个固定的标准。
02
“目的”如何评判
目的落空理论源自德国的个人损失理论,在判例中可以得出,衡量个人损失即使存在双向的给付,只要被害人履行合同或者提供给付的使用价值未被实现且反对给付未能实现经济价值上的补偿,即可以构成诈骗罪。首先,被害人目的的确定应当在罪刑法定和刑法明确性的框架下运行,首先不能混淆被害人目的落空与处分自由的界限。诈骗罪的保护法益始终是财产,被害人目的落空仅作为客观经济衡量后辅助性的判断路径以解决骗取国家补贴或骗取捐款等行为。德国理论中的个人化的损失理论要求损失的原因必须是合同中明示或者默示的,例如国家财政提供农用机补贴可以说默示了其合同目的以帮助购置农用机有困难的农民、为其提供补贴,因此被害人的目的很难说被僭越了;其次,目的的衡量必须在经济损失的成就的框架下展开,用于进一步判断财产的使用价值是否实现。因此在客观的经济衡量已经可以确定经济损失后,还需要运用目的落空理论证明财产损失的存在。若仅以被害人因受欺诈而处分了财产,并以此推定行为人若认识到了事实真相则不会从事交易,那么诈骗罪就被扩张为针对交易自由和交易真实的犯罪。在单方合同类骗补类诈骗中,财产损失的考察具有优先性,因为经济财产中已经蕴含了社会目的,仅当财产损失难以证明时,可通过背后的个体化价值的未实现进行补正;最后,目的应当遵循客观目的论,不能完全依靠被害人的主观目的。目的的判断应当以社会惯常的使用目的和规律进行衡量。目的落空虽然考虑了被害人订立合同时的意志,但是合同目的不等同于当事人制定合同的动机,该目的的定义还是需要通过客观的第三人借助财产使用的秩序进行确定。同时,目的一般限定于社会、道德目的等领域,目的必须与可罚性的欺诈行为直接关联,根据“处分目的重大背离”这一学术翻译的内涵而言,“目的”应当是之于合同交易具有重大意义的。
03
目的落空理论的价值
目的落空理论在实践中的价值即在于单方给付等特殊场合,应结合财物提供方个人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是否造成了财产的损害。但是基于诈骗罪属于财产犯罪出发,仍应严格限定财产损害的发生必须是蕴含在合同目的项下的与经济价值相关的目的不达。财产损失和目的落空理论应置于两个层面进行建构。若合同的对待给付并未侵害到财产的交换价值的实现,仅仅是单纯的善意目的的落空,那么不应以刑法进行规制。
通过对于目的的限定,在认定财产损失的过程中仍然遵循社会公认的财产使用秩序和交易管理,厘清对价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的平等,其社会价值与刑事政策的实现也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维稳以及一般预防的实现。根据学者提出“政策目的落空”这一用语,可见财政补贴的特殊性,法律作为维护政治的手段,应当针对此类财政政策的诈骗行为进行严厉制裁和统一的司法标准的制定。
五
总结
针对骗补类诈骗来说,运用客观的经济衡量原则进行财产损失事实层面的具体认定,再借助社会目的落空理论作为价值判断来限缩诈骗罪处罚范围,可以避免处罚范围无限扩张同时保证骗补类案件中的财产损失的认定路径更为完善。在客观的经济衡量计算中,基于骗补类诈骗的侵害对象特殊性,不能将视角停留于财产损失方的给付,也应当将另一方的对待给付纳入财产损失的衡量中。根据财物的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为起点,以德日的司法判例为参考系,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目的落空”的实践标准。实质性地运用目的落空理论作为第二层次的判断,针对设定补贴者提供财物时的真实意图是否实现、是否造成损失作为衡量财产损失要件的补充路径,实现骗取补贴类诈骗罪的统一的司法适用,运用刑法的有效规制,有效维护财政补贴专款专用的社会目的,实现刑法在刑事政策的藩篱下运行。
★
杨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