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天刑事】帮信罪专栏 | 浅谈“帮信罪”中的明知问题

·关注公众号并留言 免费咨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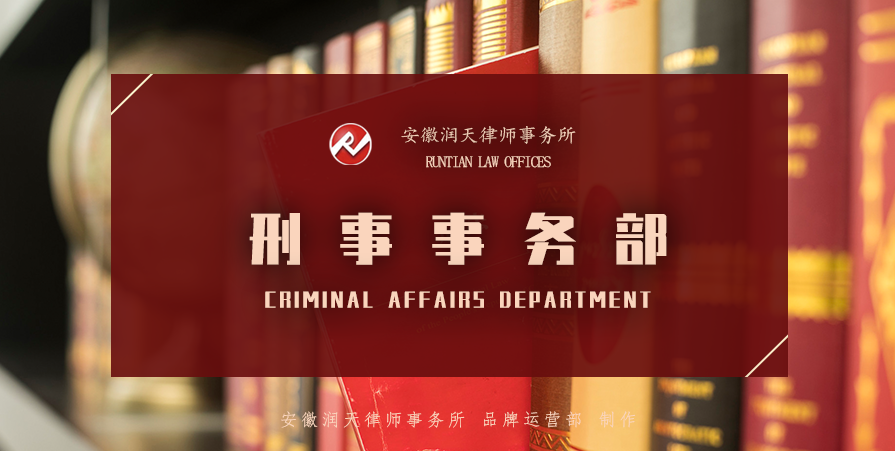
《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将“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规定为帮信罪的主观构成要件。也就是说若不能证实行为人“明知”他人实施犯罪,则不能认定构成本罪。
而“明知”的认定一直是本罪实务中的难点,这主要是由于是否“明知”会因为行为人的供述而显得极其不稳定,实践中常常需要依据客观情节对主观明知进行推定。
一、明知的认定
对于帮信罪而言,应当综合判断主观明知,重点审查行为人提供信用卡或转账的行为是否具有正当理由。特别是行为人是否具有正当理由不能仅凭其供述和辩解,应结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既往经历、交易对象、与被帮助对象的关系、提供帮助的时间和方式、获利情况等方面综合认定。
在行为人主观明知无法查清的情况下,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一条对何时可以推定行为人“明知”做出了规定:
为他人实施犯罪提供技术支持或者帮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但是有相反证据的除外:
(一)经监管部门告知后仍然实施有关行为的;
(二)接到举报后不履行法定管理职责的;
(三)交易价格或者方式明显异常的;
(四)提供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者其他技术支持、帮助的;
(五)频繁采用隐蔽上网、加密通信、销毁数据等措施或者使用虚假身份,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的;
(六)为他人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提供技术支持、帮助的;
(七)其他足以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
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关于“断卡”行动中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2022》)对于“两卡”犯罪中的明知问题做出了规定:
在办案过程中,可着重审查行为人是否具有以下特征及表现,综合全案证据,对其构成“明知”与否作出判断:
(一)跨省或多人结伙批量办理、收购、贩卖“两卡”的;
(二)出租、出售“两卡”后,收到公安机关、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电信服务提供者等相关单位部门的口头或书面通知,告知其所出租、出售的“两卡”涉嫌诈骗、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人未采取补救措施,反而继续出租、出售的;
(三)出租、出售的“两卡”因涉嫌诈骗、洗钱等违法犯罪被冻结,又帮助解冻,或者注销旧卡、办理新卡,继续出租、出售的;
(四)出租、出售的具有支付结算功能的网络账号因涉嫌诈骗、洗钱等违法犯罪被查封,又帮助解封,继续提供给他人使用的;
(五)频繁使用隐蔽上网、加密通信、销毁数据等措施或者使用虚假身份,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的;
(六)事先串通设计应对调查的话术口径的;
(七)曾因非法交易“两卡”受过处罚或者信用惩戒、训诫谈话,又收购、出售、出租“两卡”的等。
以上所述都是客观上存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行为,但无法查实行为人主观上明知的情况,如此就只能在客观要件中加码,以此“推定”其具有主观上的明知。如在“两卡”犯罪中,行为人有“出租、出售的“两卡”因涉嫌诈骗、洗钱等违法犯罪被冻结,又帮助解冻,或者注销旧卡、办理新卡,继续出租、出售的”特征及表现的,便可以判断其主观上的明知。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讨论的前提是行为人的主观明知无法查明,若已经有证据能够证明行为人主观明知,则无需具有以上情形,只要客观上实施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的行为,并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就可以认定为构成本罪。
二、“明知”的范围
(一)“明知”不包括“应当知道”
“明知”为“明确知道”,而非“应当知道”。帮信罪本身是一项故意犯罪,而只有主观“明知”才能到达故意的程度;在“应当知道”的情况下实施了帮信行为,仅仅只是过失。换言之,若只能证明行为人“应当知道”,但无法达到“明知”的程度,则不能认定其构成本罪。
(二)“明知”不包括“可能明知”
实务中部分判决书中仅仅记载行为人“明知他人可能进行犯罪”。如(2020)豫1326刑初223号刑事判决书中,仅记载被告人李某某“明知对方可能用于违法犯罪”,并未描述其他任何可以认定、推定为“明知”的情形。“可能明知”与“明知”的程度明显不同,据此认定行为人具有主观罪过值得商榷。
(三)“明知”不包括“明知可能”
仅仅认识到“实施犯罪的可能性”,不宜轻易理解为“明知”,否则会将大量中立帮助行为不当认定为帮信罪。如电信网络服务商等的行业人员,在工作中往往会接触到大量利用信息网络犯罪的人员,其很容易意识到客户具有实施犯罪的可能性,但只要其办理业务的行为符合行业规定,即使客户构成信息网络犯罪,也不应当认定行为人主观明知、构成帮信罪。否则,不但会大幅增加信息网络服务业的审核难度与成本,也会造成公民办理相关服务的难度与日俱增,同时甚至可能造成公民信息的泄露。
三、明知内容的范围
(一)“实施犯罪”的理解
《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查证被帮助对象是否达到犯罪的程度,但相关数额总计达到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标准五倍以上,或者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应当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有人认为这意味着本罪不再需要查证被帮助的人的犯罪情节,也不要求被帮助对象实施了犯罪行为,只要帮助行为本身达到了本条规定的程度,就可以构成本罪。
这一理解明显有误,任何解释不能超出法条本身可能具有的含义,《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明文规定了“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所以明知的内容必然要包含在“实施犯罪”的含义之内。
1.“实施犯罪”包括构成犯罪
若被帮助的人已构成信息网络犯罪,自然属于“实施犯罪”的范围,此处不再赘述。
2.“实施犯罪”包括虽未构成犯罪,但属于分则规定的行为
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行为独立成罪,一是为了有效抑制实施某种更严重的犯罪;二是这种帮助行为造成的独立法益侵害已经达到了需要科处刑罚的程度;三是因为信息网络犯罪的特点造成了将帮助者作为上游犯罪共犯进行处罚,往往存在着共同故意等方面调查取证困难。
综合以上原因,如果将“实施犯罪”仅仅限定为“构成犯罪”,并不符合本罪的立法初衷和目的。
并且,只要被帮助的人着手实行了犯罪,即使没有达到构成犯罪的程度,也不能否认其“实施”了犯罪,如诈骗未达到数额较大等。同时,实施了分则规定的犯罪行为,也属于“实施犯罪”的字面含义之内。
3.实施犯罪不包括犯罪预备
实施犯罪要求至少着手实行了犯罪,如果将预备行为评价为“实施犯罪”,明显过于扩大了本罪的犯罪。
当然,行为人对预备行为的帮助只是不构成帮信罪,其是否构成其他犯罪、是否应当以其他犯罪的共犯予以处罚,应结合具体情形予以判断。
4.实施犯罪不包括仅仅是行政违法的行为
实施了分则规定的犯罪行为已经是“实施犯罪”解释的最大限度。对于分则未做规定,仅仅是对他人的行政违法行为予以帮助,不应当构成帮信罪,如帮助网络招嫖等。
(二)明知的范围
当行为人明确知道被帮助对象犯罪的性质时,自然属于“明知”的范围。
然而,信息网络犯罪相对于传统犯罪而言,行为人之间的意思联络往往较弱,对其“明知”的范围也不应当仅仅限定于上述情况。所以,如果行为人只知道被帮助者实施了信息网络犯罪的行为,不影响主观明知的认定,不需要知道具体的犯罪性质;并且,不要求行为人明知被帮助者实施的行为达到犯罪的程度,只需要明知其实行了刑法分则规定的行为即可。
(三)明知的程度
明知应当是“大概率事件”,即知道被帮助人的大概率要实施犯罪。如在“两卡”犯罪中,很多人出售、收购银行卡并非用于犯罪行为,而仅仅是为了规避实名制,此时据此推定行为人明知明显并不妥当。
此外,既然是依据大概率事件推定行为人明知,那自然还存在行为人不明知的小概率事件。此时,应当允许行为人提供反证,只要能达到形成合理怀疑的程度,则应当依据存疑有利于行为人的原则,认定行为人并不明知。
王 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