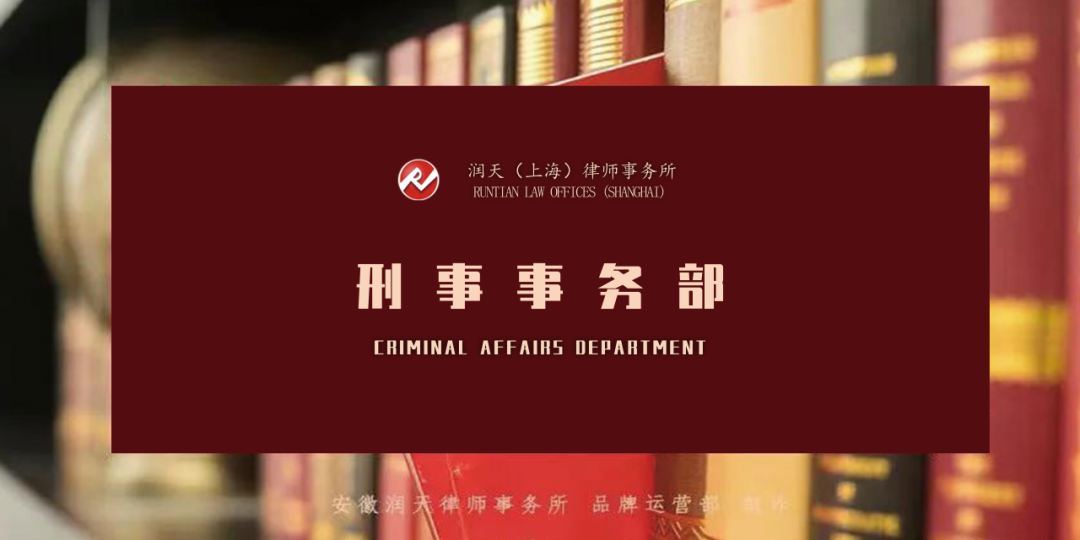
职务侵占罪之何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随着互联网电商产业的快速兴起,快递配送员侵占快递货物的事情也随之增多。各地域的法院对于快递员侵占快递货物的案件会有不同的处理结果,未形成统一的标准。为了能对职务侵占行为有更准确的定性,首先就要准确解读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实践中对于职务侵占罪的客观方面的认识存在一些争议,如何理解职务侵占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准确区分本罪与他罪的关键。本文先从典型案例入手,深入解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构成要件,从剖析理论争议点着手分析,提出对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应有内涵的理解,进而深入解读对“职务”的理解。
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实务中的争议
职务侵占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构成要件是区分本罪与他罪的关键,对此构成要件的理解不同会直接导致实务中对类似案件的定罪不同。通过查阅案例发现,有些相似的个案却出现判决不同罪名的结果。因此,需要严谨的、准确的界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构成要件的边界。通过查阅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川刑提字第2号案例。原审被告人杨某为顺丰公司的运作员,在四川省双流县公兴镇“成都中转站”上班,负责快递包裹的分拣工作。2013年11月15日凌晨3时许,杨某正值夜班,在其负责的工作区域分类整理快递包裹的过程中,将其直接经手整理的一外有“M”标志、内为一部小米手机的包裹窃取,非法占为己有。同月20日,公司发现包裹丢失,随即便调取了该中转站的监控录像,经查,该包裹被该公司的工作人员杨某窃取。26日顺丰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报案的当天下午,公安机关出警,在抓捕了被告人杨某后,在其身上便搜查出了被窃取的小米手机,后在杨某的居所内找到了该手机的充电器以及发票。经鉴定,被告人杨某窃取的手机价值1999元。被告人在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窃取包裹的事实,并向顺丰公司照价赔偿了1999元。
本案经过前后长达20个月的庭审,共进行3次公开审判,分别由三级检察院参与抗诉,三级法院开庭审理,最终以宣告杨某无罪结案。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人杨某构成盗窃罪并处罚金3000元。宣判后,四川省双流县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抗诉理由如下:同为双流县人民法院审理的被告人贾有福盗窃案,两案盗窃金额和量刑情节相当,而判决结果却差距明显,特此提请二审法院重新审理并改判。二审法院经审查认定,原审被告人杨某在其经手分拣快递包裹过程中秘密窃取包裹的行为,是利用了经手单位财物的职务上的便利,其行为具备职务侵占的性质。因其金额未达到职务侵占罪的量刑起点,遂二审法院判决宣告原审被告人杨某无罪。该案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终审裁定,维持二审判决。
案例中,一审和二审法院的判决结果截然不同,侧面反应出实务过程中对职务侵占行为与盗窃行为的认定存在偏差。对于职务侵占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解读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对“职务”的理解有不同解读。
二、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应有内涵的理解
张明楷教授曾指出,刑法的目的就是保护法益,想要解释某个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必须从该法条所保护的法益内容出发,再结合法条的刑法条文,去探讨个罪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具体含义及内容,推导出对于犯罪构成要件理解的差异,进而会影响对于个罪的理解和适用。要想科学界定职务侵占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必须先分析职务侵占罪的法益内容。本文对于职务侵占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研究有助于职务侵占罪的具体行为方式认定以及了解本罪的客观方面。
有关职务侵占罪所保护的法益内容存在单一法益论和双重法益论两种学说,单一法益论认为职务侵占罪所保护法益只包含一种法益,其法益内容为“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财产所有权”,这是目前我国刑法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版。而与之相对立的双重法益论的学者认为,职务侵占罪所保护的法益内容除了单位的财产权利之外,还包括“本单位的公共权力”或“本单位的管理制度”。参见夏勇、刘伟琦:职务侵占罪双重犯罪客体之提倡,人民检察,2014版。赵秉志:侵占罪专题整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版。两学说对立的根本原因是,对于职务侵占罪的理解依据不同,一方是以贪污罪作为参照来理解职务侵占罪,一方是以侵占罪作为参照来理解职务侵占罪。
张明楷教授指出,各种具体的犯罪,都会被划拨为某一类罪,对于类罪的同类法益,在刑法中都会有明确或具有指示性的规定,那么要探讨个罪的法益内容,只要明确个罪所属的类罪,便可通过类罪的同类法益的内容,大致明确个罪保护法益的内容。根据此逻辑,职务侵占罪属于侵犯财产类犯罪,根据类罪的同类法益内容,可以明确职务侵占罪规定的法益为财产,或者说其保护的法益必然包含财产。
双重法益论者认为职务侵占罪是从贪污罪中分离而来,两者殊途同归。对此得出以下两点:第一,双重法益论者认为,单一法益论违背了立法者的初衷,完全忽视了职务侵占罪侵犯的单位公权力法益。单位的职工在履行职务的同时也在行使单位公权力,如果行为人在行使单位公权力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侵占本单位财物,必然会造成单位财产利益的损失。由此可以明确,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不仅仅是侵犯财产法益的行为,也是侵犯单位公共权力法益的行为。第二,双重法益论者认为,刑法个罪所保护的法益与犯罪构成要件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呼应的。例如,抢劫罪所侵犯的是双重客体,即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将抢劫罪所保护的法益对应到该罪的构成要件之中,即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对应人身权利法益,而“抢劫公私财物”则对应财产权利法益,体现出犯罪客体与行为方式之间是一一对应的。职务侵占罪的客观行为方式包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为己有和数额巨大(数额不予讨论),而单一法益论者认为职务侵占罪的法益仅为财产法益一项,因此无法一一对应。因此,只有“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对应财产法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对应公共权力法益,才能将两者一一对应,使之相协调。
作者则认为,双重法益论者的上述两个理由略显牵强。单位的公共意志是为了维护本单位的财产利益,那么作为体现单位意志的“单位公共权力”仅是手段,其存在目的必然是为了保护单位财产,所以在财产法益之外没有必要将单位公权力法益单独列出加以保护。如果赞同双重法益论,会违背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同时也无法对于职务侵占罪的最高法定刑低于盗窃罪、诈骗罪等普通财产犯罪的最高法定刑给予合理解释。职务侵占罪的最高法定刑为十五年有期徒刑,而盗窃罪、诈骗罪的最高法定刑为无期。相较于普通的财产犯罪,职务侵占罪如果多保护了一项独立法益(单位的公共权力),其法定刑应高于盗窃罪、诈骗罪,可事实并非如此。张明楷教授指出,当解释者对于刑法条文的解释不符合刑法正义时,与其在得出结论后怀疑刑法,不如怀疑自己的解释能力和结论;作者在聆听单玉成律师刑辩全流程分享课程中的《刑辩分类》5-6 发现,单老师是比较认同张明楷教授提出的指导方针,同时认为类罪的刑罚轻重之间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法定刑的设定不仅要考虑到不法行为对法益的侵害程度,还要考虑到对犯罪的预防难度以及打击难度。对此,作者认为上述双重法益论需要调整。
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学说争议
利用职务之便是职务犯罪的典型特征,也是成立职务侵占罪的必要条件,同时还是在实务中区分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的关键因素。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目前并未规定职务侵占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具体边界。理论界在理解职务侵占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含义时大多是参考贪污罪和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两部司法解释,对其含义的理解众说纷纭且相互对立,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职权便利说
认为本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就是行为人利用其在管理本单位生产、经营的过程中所拥有的指挥、领导、监督等权利。参见张翔飞:商业侵占罪初探,法学 1997。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职务侵占罪是从贪污罪中分立而来的产物,两者如出一辙,本质上两罪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构成要件的含义是一致的,所以应当参考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内涵来理解职务侵占罪。此种学说直接将“劳务上的便利”完全排除在了“利用职务之便”的范围外,行为人必须具备指挥、领导、监督本单位财物的权力,才有可能构成职务侵占罪,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含义的范围进行了限缩。
(二)工作便利说
认为本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公司企业等单位中具有某种特定职务的工作人员享有的其特定职务带来的权力和地位;或者指单位的一般职工因其工作关系而熟悉本公司的环境,凭借其具备单位工作人员身份的条件,任意进出相关部门,较其他人更容易接近作案目标和对象,从而侵占本公司的财物。参见孙国祥:关于侵占罪的几个问题,《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6 春季号。该观点对于职务侵占罪所规制的范围进行了扩大。
(三)职责便利说
认为判断本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范围应当基于工作职务的具体责任范围,以具备处分本单位财物的权限为出发点,如果行为人对本单位财物具有一定的管理权限;或者是因其职务而享有的职权便利,那么该行为人便可认定为具有职务上的便利。参见肖中华、闽凯:职务侵占罪认定中的三个争议问题剖析,政治与法律,2007 版。该观点认为对于本单位财物具有一定管理权限便认定为具有职务便利的说法有些不妥。比如某企业的小车驾驶员将其具有一定管理权限的财物(如洗车的刷子和清洁液)窃取出企业,通常情况下,该驾驶员的行为会定性为盗窃罪,而不会被认为是利用了其直接经手公司财物的便利侵占单位财物构成职务侵占罪。
(四)控制支配说
认为将本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理解为“利用在单位中因承担有关事务所获得的支配、控制本单位财物的地位”。具体理由是:第一,“职务”的范围,以侵犯单位公共权力法益为原则。第二,对本单位财物具有的支配控制地位,为侵犯单位公共权力法益提供可能性。参见刘伟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司法误区与规范性解读—基于职务侵占罪双重法益的立场》,载《政治与法律》2015 年第 1 期。认为:本罪“职务”范围的实质标准是在单位中从事支配控制本单位财物的事务,倘若行为人在单位中从事的事务具有支配控制本单位财物的地位,则该事务属于本罪之“职务”,倘若行为人在单位中从事的事务不具有支配控制本单位财物的地位,则该事务不是本罪之“职务”,这里的支配控制地位可以表现为占有、保管、处分等多种形式。
(五)主管、管理、经手财物便利说
认为职务侵占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单位工作人员的职权或者职务而形成的主管、管理、经手本单位财物的便利条件”。贪污罪中的职务之便和本罪中的职务之便含义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主管财物,是指单位工作人员在职务上对本单位财物具有购买、流向、调配等决定权力。管理财物,是指单位工作人员与本单位财物之间形成的保管与管理关系。经手财物,是指单位工作人员因其职务而支配、使用、领取本单位财物的权力。故而,因单位工作人员的职务而主管、管理、经手本单位财物的,都能认定为本罪的利用职务之便。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版。在司法实践中此观点经常用于处理相关案件,但要想厘清职务侵占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含义,还需明确“职务”的具体内涵。
四、对“职务”具体内涵的界定
参见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2)杭江刑初字第513号。被告人常某是浙江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快递员,2012年2月5日10时许,被告人常某在派件期间,私自将装有苹果四代手机6部的包裹拆开窃走其中5部,后将该包裹重新封装送至收货人处。被告人常某及辩护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均无异议,但被告人辩解其行为应构成职务侵占罪。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常某对密封的包裹内的财物并不具有直接经手且管理的便利,只具备作为快递员配送货物的便利条件,进而窃取他人财物,法院判决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
而在犯罪情节相似的另案中,法院判决结果却有不同之处。
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沪二中刑终字第1170号。被告人陈某某于2013年10月起担任上海市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快递员一职,负责货物的递送工作。2013年10月上旬某日,陈某某按照公司的派件安排,将快递件向王某某进行派送。陈某某利用上述职务之便私自拆开装有和田玉一块的快递包裹外包装,并窃取该包裹内物品价值45000元的和田玉一块。而后用类似大小的石头替代和田玉放回包裹内,随后将快递交付于王某某。王某某打开包裹后发现货物被掉包,而陈某某对其质疑予以否认,并后于12月7日离职。同年12月30日,陈某某至王某某店铺内声称找到了该件和田玉雕手把件,并向王某某索要好处费。在二人沟通中王某某发现陈金满才是始作俑者,陈某某因露馅害怕遂即交出随身藏匿的和田玉。公安民警接警后赶至现场将陈某某传唤至公安机关。原审法院认为,原审被告人陈某某身为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二审法院认为,原判认定上诉人陈某某犯职务侵占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定罪量刑均无不当,维持了原判。
上述两个案例中,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实质上已经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该行为最终未定职务侵占罪,反而以他罪定罪处罚的原因就是对“职务”内涵理解不够明晰。在我国,有关“职务”的概念最早起源于行政法学领域,参见林岚:论我国刑法中的“利用职务之便”,西南政法大学2012版。其主要含义是指行政主体在机关或事业单位中所实施的国家和社会管理的行政职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行政职务。
一种观点认为,“职务”等同于“职权”,是指在权力范围内具有管理性的活动,也称之为“管理性事务说”。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版。主张此观点的学者认为,职务侵占罪与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含义本质上是相同的,“职务”有权力性和管理性,而不具备此性质的一般劳务则不是职务侵占罪中的“职务”。
另一种观点认为,“职务”某种意义上是等同于“工作”,具有持续稳定的特征,也称为“持续性事务说”。换言之,单位对职工临时性委托的超出持续稳定工作内容以外事务不属于职务的范畴。参见尹琳:刑法上职务便利与工作便利的区别必要性辨析,政治与法律2015版。主张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判定职务的范围不能仅局限于形式层面,还要从实质层面着手,判断职务的实质性依据是工作内容本身,而不是判断是否具备工作人员的身份,但凡持续且稳定地从事单位工作或履行工作职责的,在实质上都属于职务范畴。
由于对文字理解的差异导致了上述学说的分歧。通过查阅字典,对于“职”的解释为分内应该做的事。而词典中对于“职务”一词的解释为职位规定应当担任的工作。对“职务”的理解,一方面是,职务是产生职权的基础,其含义相对于职权来说,具有更宽广的范围,换言之,拥有职务的工作人员未必拥有相应的职权。仅从文义角度解释,“管理性事务说”将非权力性或非管理性的事务排除在职务含义范围之外,其理由并不充分。另一方面,职务不仅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还具有临时性的特征。在生活中,职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指在某个时期内持续且反复的从事某类工作,但在实践中也不排除临时性的工作突然出现,临时委托他人来从事自己无法完成的职责范围内的工作的情形也较为常见。如果行为人接受单位临时委托处理公司事务时使用虚假票据骗取到单位的款项,依据“持续性事务说”的观点,便无法构成职务侵占罪,但虚假报销行为因包含职务属性理应按照职务侵占罪论处,如仅仅以没有持续稳定性便将虚假报销排除在“职务”范围外则略显不合理。综上,“职务”包括一般劳务行为和管理性行为,同时还应具有持续稳定性和临时性的特征。
五、结尾
张明楷教授指出,法律条文只有当它处于与它有关的所有条文的整体之中才显示其真正的含义。故而,还应充分理解职务侵占罪中该要件的独特性。关于职务侵占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涵义解读大多参照贪污罪,职务侵占罪中关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内涵是相对独立的,并不能完全照搬贪污罪的相关标准。贪污罪在创立之初便强调“从严治吏”的精神,其立法意图不仅在于保护公共财产,还突出强调一种职权。而职务侵占罪没有“从严治吏”的需求,其更加强调的是行为人基于职务关系而直接占有财物。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得出,职务侵占罪所保护的法益仅仅是财产,并不包括其他内容。据此推断出,职务侵占罪就仅仅只是一个单纯的财产犯罪,并不能依照贪污罪作为参照系来理解职务侵占罪。《刑法修正案(九)》对于贪污罪的情节和数额做出了修改,新增了“其他较重情节”、“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等规定,且分别将其与数额并列。所以,判断某行为是否为贪污罪,一方面要看犯罪数额,另一方面要看是否侵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廉洁度。而职务侵占罪的入罪模式并没有情节标准,仅以数额为入罪标准。所以,职务侵占罪所侵犯的客体当然只包括财产。职务侵占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应理解为行为人基于其工作职责而负有占有、控制本单位财物的地位,且行为人最终占有财物与其工作职责带来的便利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本章之初所提及的杨某职务侵占案中,正是因为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范围的不合理解读,造成了同一案件出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不同判决。被告人杨某为顺丰公司的工作人员,负责快递包裹的分拣工作,从形式层面和实质层面进行分析,被告人杨某都具备顺丰公司工作人员的职务。杨某对于传送带上的快递包裹具有直接的控制地位,因而充分享有职务上的便利条件,其作案过程也正是利用了其经手财物这一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单位财物。被告人杨某非法占有公司财物与其经手快递包裹这一便利条件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行为完全符合职务侵占罪的犯罪特征,完全不需以盗窃罪论处,避免承担更重的刑罚,由于引起犯罪金额尚未达到职务侵占罪的定罪起点,故不以犯罪论处。
作者介绍
李诗男 见习生




